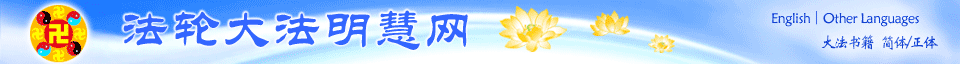【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九日】看到明慧网2008年12月11日《劳教所警察承认在法轮功学员的饭里下药》一文,使我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我在被迫害中经历过的一次神志不清和上文说的情况一模一样。在北京女子监狱被残忍迫害的经历在《京城的人间地狱》中介绍过,下面主要说说这次被迫害的神志不清、身不由己的情况。
北京女子监狱的酷刑“脱敏”(对全身所有部位进行踩、压、掐、折、击打等折磨)使我脊椎两处骨折,此后又昼夜罚站、不准睡觉、被打骂侮辱等等。在这种折磨中我坚持了一个月,后来因为我正念不足,感到身体实在承受不住,被迫违心的妥协。一个月后(也就是2004年7月初),我声明重新修炼。面对的是更为残酷的迫害环境,我坚定对大法的正信不动摇,走过了艰难的四个月,在此期间我虽然吃了许多苦,但我始终头脑清醒、意志坚定。可是到了年末,不知为什么却突然间意外的出现了神志不清的情况,而且伴有全身剧痛的症状。在这种极不正常的状态下,恶警急不可耐的强迫我做这做那,使我摔了跟头。这几年来我反复向内找,但我却始终搞不清那个神志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邪党恶徒们给人饭里下毒药,这是我当时怎么想也想不到的。
为了达到罪恶的目的,邪党人员竟用如此卑鄙下流的手段来迫害我们修真善忍的好人,真是天理不容。2004年,在北京女子监狱,由于我坚定修炼,恶人们对我恨之入骨,我成了那里的“名人”。2004年5月中旬,十分监区队长田凤清用“脱官服”为条件做抵押(是她自己说的),到女监狱政科申请对我进行肉体迫害。也就是说,在我腰背两处骨折的重伤、又经过近一个月的各种折磨后,再次加码:申请持续昼夜罚站,直到转化为止。田凤清还公开说:“真后悔不该把这个老太太接到十区来!”
2004年6月初,我因腰伤疼痛到监狱医院看医生,宋大夫看了我的腰后,问我:“怎么会搞成这样?”我避开包夹李小兵,告诉医生说:“是她们‘转化’给搞的。”医生当时没有作声。2004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被叫到大厅,副中队长闫春玲对我说:“周监(女子监狱副监狱长周英)要和你谈谈。”可能是医生把情况反映了上去。实际上后来周英并没有来见我。又一天,闫春玲告诉我:“是田凤清下令‘脱敏’的;现在靳红卫(主要打手)也知道错了。” 而田凤清却当面对我撒谎。当我向她叙说当天她们如何施暴和我的痛苦时,她说:“这事我不知道。”还说:“你当时怎么不喊哪?” 甚至还挤出几滴眼泪来以表示对我的同情。我看见了,是田凤清当天值的班。其实我当时就知道,是她亲自指挥了那场暴刑。2004年7月初,田凤清突然被调走。
2005年9月,女监大面积食物中毒,我也因此住院了。
2007年6月初,我的朋友到女监来看望我。在我没有到达之前,狱政科的张科长给我的朋友介绍说:“这老太太在监狱里挺出名的。”由于我坚信大法,成了一些邪恶狱警的眼中钉、迫害的重点,尤其在十分监区是她们迫害的焦点。
在当时,65岁的我,已经走过了人生的许多艰难路程,在没有修炼之前就已经经过了许多大灾大难,但是,不管灾难多大,我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神志不清的现象。
在2004年12月,虽然对我的种种迫害持续不断,但我坚信大法不动摇,头脑始终是清醒的,怎么会突然间出现神志不清、身不由己的状况呢?这是个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现在来看看当时狱警们的一系列行动:
2004年11月末,狱警们看到历经四个月,对我的“转化”久攻不下,更阴毒的迫害手段在郑玉梅她们的策划下产生了:很明显,她们要不择手段的达到在年底前转化的目的。于是,副中队长闫春玲、小队长申艳秋、吴蕾三个人直接从后台走到前台,赤膊上阵了,她们亲自对我进行了一系列挖空心思的迫害:
24小时一秒钟不间断的所谓“法律”审讯,即“熬鹰”,纯粹是为了摧毁我的意志、消耗我体力的卑劣手法。当时我对申说:“你是个很能胡搅蛮缠的人!”她们把我拉到每个班的门口,让班里人骂我;把我揪回班里,逼着班里人批斗:打骂、推拽、撕衣服,做什么的都有;大冬天‘帮教们’不准我穿棉衣、棉鞋,还要逼我长时间拔军姿、走正步;郑玉梅亲自下令让全监区近百人一起罚站,不让她们睡觉,以此压我‘转化’;她们对我宣布:“从现在开始,24小时之内只准去一次厕所。”就在那一天中,23个小时以后她们才允许我去了一次厕所。
她们让“帮教”带我在屋子内转圈,转圈时喊口号,口号的内容,由无关紧要到要决裂大法。看来她们是要看我的头脑是否还清醒。当时我已经发现我的状态不正常:出现了身不由己、心口不一的现象,对她们让喊的口号,心中说:‘不是这样’,可是我的嘴却不听我的使唤。而我当时又改变不了这种被牵着走的状况。
过了一天,三个狱警同时出现在我面前 ,闫、吴站着、申蹲着。申仰着头用力盯着我,并且一遍一遍的喊:“你是岳昌智吗?”、“岳昌智回来吧!”,“岳昌智回来吧”;当时我比较清醒,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对此很反感,就说:“我就在这里!”过了一会儿,她们休息的时候,我对申艳秋说:“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她说:“为什么?”我说:“你们是长官(我口误把警官说成了长官)。”她突然大哭起来,大喊:“她说我是长官了!”并哭着喊着冲向大厅。当时在大厅有七、八十人正在干活,她对着干活的人大哭大闹,谁劝也不行。这时我也来到大厅,现场管生产的肖队长看见我出来了,走到我面前,问我:“你转(化)不转?”我回答:“我不转!”肖说:“不转,回去!”我就回到了房间。过了一会儿申也回来了。她进屋后脱下了上衣,用劲甩在沙发上,哭着大叫:“你给我写‘决裂书’!!!”我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就是不写!
到了夜里,持续被罚站的我,又出现了神志不清的现象,而且这次较上次更严重: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很陌生,我不知道我身在何处,感觉好象在地下室,实际一直在四楼十分监区,没有动地方;我不知道去厕所的路怎么走。(我来到十分监区已经十个月了,怎么可能不知道去厕所的路呢?可是当时就是那样。)更为严重的是,我不但神志不清,而且同时伴有全身剧烈疼痛、真的无法承受,真的是生不如死。
大约深夜两点多,闫春玲进来了,她躺在沙发上,双脚横在沙发的扶手上,用冰冷的目光看着在痛苦中挣扎的我。这个向来以和善面目出现的、自称“保护法轮功学员的”、并得到过许多法轮功学员的好评的人,此时却完全现出一付凶残面孔。我在极度痛苦中,她不但不准我蹲一下缓解痛苦,相反却疯狂的强迫我写“决裂书”,厉声命令我写东西。那是我从来都不想做、永远都不要做的事!我心中想:不写!但手却不听我的指挥。不一会儿,申艳秋又进来了,还要逼着我再写上“不要生命的永远”!我的心中说:“怎么能不要生命的永远呢?!”可是我心中的这个声音太弱,主宰不了我的手。就这样,我象个木偶似的,被人牵着、机械的做着她们要我做的一切。此后的一天中,她们仍不准我有任何休息的机会,始终不让我坐、蹲、扶、靠、各种休息,即使写东西也必须站着写,甚至同一个东西逼我反复抄。很明显,就是消磨时间,就是不让我休息!直到又过了24多小时后,她们才让我有了点休息时间,休息后我清醒过来了。我懊悔莫及,痛不欲生,我竟做了这可耻的事!
我的这一切不正常情况,‘帮教’们也看到了。‘帮教’中有个叫郑燕苹的问我:“你是不是主元神不在位了?” 我点头。后来,她看我情绪非常消沉,就又问:“你是不是想‘翻车’?” 又说:“想翻就翻,我们也都翻过。”
这种迫害,对精神、心理的伤害与打击是巨大而无法言表的。有位同修建议我写揭发信。过去我不想写,是因为我认为监狱都是一窝黑,写了也没有用。而这次,我想我要揭露邪恶、曝光迫害,我开始动手写了。在那种环境中,要想写点东西,尤其是法轮功学员写信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而且随时都会搜监,写了也会被抄走,而且会遭到新的迫害。但是,这一次我写成了。
2005年8月底,历时近两个月,这期间奇迹般的没有搜监,我写给周英副监狱长的长长的一封信和一份重返修炼的声明完成了,并成功的投进了监区筒道里的监狱长信箱。信中我把十分监区前后两次对我的残酷迫害及前次使我承受不住,后来让我神志不清等情况都揭露了出来;同时声明:强制下所做的一切都不算数!一切强制下的言行全部作废!谁也改变不了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决心!
信发出时,监区的监控室就看到了,接着我就又被看了起来。 这一次我是带着强大的证实法、反迫害的正念,我抱着即使失去人身也绝不再违心说话的决心与她们座谈的。相反,她们没敢把我怎么样。座谈进行了九天时,参加座谈的人觉得没什么可谈的了,她们还说:“你很坦荡,我们很佩服你。” 其中一人又说:“我看到有许多小金星从你身上掉下来。”2004年年底的迫害过后,很快,三个直接参与迫害的狱警都被调走了。
我那次的神志不清,如果她们不对我做手脚,她们为什么会有那种反常的表现? 如果她们不做手脚,我为什么会出现那种不正常状态?极有可能是邪恶之徒往我的食物中放了药物才造成这种状态。其实无论恶徒是否下药,就从我一个身心健康的人被迫害致神志不清这一基本事实,就可以看出中共洗脑的野蛮和残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