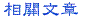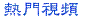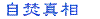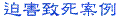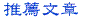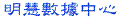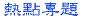我在山东王村劳教所的惨痛经历
下面我简单的说说自己经历的迫害,只提牵扯我被迫害到王村劳教所的部份恶人:邪党村支书记(乌好吉)、枳沟派出所长(孙××)、后上任所长(梁××)、诸城国保恶科长(曹锦辉)、公安局恶队长(朱鹏德),这五个中共邪党各级邪恶之首,用尽毒招迫害我放弃信仰,借机升官发财,真的是从经济上、精神上、肉体上对我迫害。
一、邪党村支书记对我的迫害
山东诸城枳沟镇薛家官庄村邪党书记乌好吉,九九年以来紧跟江氏流氓集团将我关押在村办公室五个多月,不给床睡,我还有儿子在身边,小孩那时才两三岁,有时不许上厕所,包括我儿子。吃不上饭有时候大伯嫂送点,一二月份吃冰馒头、喝冰水,睡水泥地面,加上那些轮流包夹的人恐吓,还有派出所膀粗腰圆的恶警一来就是五六个,对我狂吼怒叫的,小孩子最后吓得患了恐惧症,只要有车声就哭着说:妈,他们又来了!那眼神恐惧慌张、脸色黄白、无处躲藏无助绝望的样子,可怜至极啊。
后几个月,乌好吉派光棍看守我,有一次晚上八九点钟,光棍心怀不轨拽我的衣袖,我吓的用长椅挡在门口一夜未眠。天亮我对乌好吉说这件事,他不以为然,狡诈地狞笑着。五个多月下来我娘俩骨瘦如柴,原胖胖的儿子只剩皮包骨,走路都走不稳。
放回家也没安稳过,他派了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监视我。有时走娘家,他们都跟到我娘家,赶集就跟到集上,后来我揭露他在犯法,限制我的自由权,他变换了更无人道的手段,只要我去了什么方向他就给什么乡镇政府或派出所电话诬告我,这一下折磨我更狠,因此我被许孟派出所、院西、五莲“六一零”、枳沟派出所,诸城公安局、看守所、洗脑班都迫害过,每次都是挨打骂,诸城国保的曹锦辉喝得醉醺醺地打我两腿内外,屁股全成紫色的了,一边打一边问还炼不炼,炼就打直打到他累得不行了才罢手。
乌好吉的恶行遭到恶报。他有一儿一女,其儿小名泉城,大名乌忠,十六岁,在枳沟上初中三年级,女儿近况不详,其妻恶毒地骂法轮功创始人,现已遭恶报,割子宫瘤。乌好吉有姊妹八九个、其中与他邻墙住的亲哥为了义务工参与监视我,其哥口吐白沫差点没命,其侄女在街上一边钩花一边监视我、得怪病巫医神汉各医院跑了一年治疗。
二、遭诸城国保恶科长曹锦辉迫害
曹锦辉此恶人,没有他不打的人,其中有四个法轮功学员被他打死,无数人打伤,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因他迫害,绝食抗议,因绝食肠内无物,后被曹打伤死在医院里,法轮功学员家人告曹,死者冰在太平间,那时上哪告也无人管。曹锦辉喝醉酒时自己说的:人肠子是好吃!瞧白的肠子真鲜。这就是江泽民的魔鬼干将!恶事累累、血债累累。
曹专门住在国安宾馆三楼,设有铁椅子、电棍子、胶棒子等,窗户用窗帘挡得严严实实的,让人的感觉就是死了也没人知道。他把我铐在铁椅上,四肢铐在四处固定,派人先看着,后由于我上厕所撞晕了,他把我送到洗脑班迫害,还是关在三楼,二十四小时看守我。他们多人轮班,我好不容易找了点空想顺下水管逃走,马上被我村妇女主任和洗脑班的人喊着找人,吓得我没来得及抱水管就跳下三楼,摔得身上脊椎骨、双脚后跟、骨盆、肋骨粉碎性骨折。数小时后才送我去医院,给我丈夫传个信后扬长而去,再不闻不问。
我瘫在床上四个月,大小便不通,靠插尿管排尿,大便一个月没有,后来只有一粒圆球还得用手抠,每次尿管只用五天,没有一点消炎药,撤了尿管我就再不想用了,肚子胀得跟怀孕一样,只有皮。骨头痛得我爬也爬不动,汗水泪水交织在一起。丈夫还有四五岁的孩子要照看,家啊已不象家,他们苦死了!丈夫有时半夜冒着雨,七里山路往返十四里给我买尿管!
我死而复活,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大小便还失控,乌好吉又伙同诸城公安局(朱鹏德)将我送往淄博王村劳教所。
诸城公安大队长朱鹏德,阴险而毒辣,不知把多少诸城的法轮功学员送监狱、劳教所等各种魔窟迫害。零一年冬天的下午,朱带领一伙恶警,未经任何手续和证件将我绑架。我在诸城看守所过了一夜,天刚亮朱鹏德就将我与另两个法轮功学员送往王村劳教所。当时劳教所不收我们,朱说尽好话,用尽办法,不知用了什么手段,我被送到五大队,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恶队长曲秀英。
三、王村劳教所的惨无人道
曲秀英开始用伪善来欺骗我,给我奶喝,我不喝她就凶相毕露,手里拿着针要给我打针,我否定她,她派来一组六七个人轮番攻击我,不让睡觉,让我坐在三条腿的硬板凳上,闭眼就打,不许我说话,只许她们说,还得让我回答,不答就打,让我骂师父。我不从,她们冻我,本来我就尿裤子,就更冷。轮番几天后,我的大脑开始迷糊,加上那里面时不时的惊叫声,更显得阴森恐怖。有一个学员被她们逼疯了,越是半夜叫的越多,哭喊着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我问她们那人怎么了,她们说:“不要问,好好配合抓紧骂你师父,不然的话那就是样子,你不‘转化’我们拿不到奖金,打死白打死,不配合关你禁闭室,站不直蹲不下,铐着拉撒在里面。“
我被强制坐得臀部烂了个窟窿流脓水,她们使酒精洗我也不知痛,擦那种紫药水我也没有知觉。她们又让我站着,轮一个人轰炸一番,不让我睡,她们睡完换班来折磨我。我的腿脚肿的没有原样了,脑袋不知道哪是哪了,一会儿觉得在家里,一会儿觉得在集上,一会儿觉得在单位,好好想想也搞不清在哪儿。
我对曲秀英说她们迫害我,曲说那你骂你师父不就没打你的了。我也说了违心话,那种心情犹如刀割,而每次承受到极限时,就如同被刀割般的说着违心话,过后我说我师父没有一点错。曲对犯人说:“你们‘转化’不了她就别想到期回家。”曲让那些被“转化”的每天写很多诽谤法轮功师父的文章,重复着那些谎言。而我的精神与体力都到了极限,加上骂自己的恩师,那种心情真不如马上死掉。可是曲秀英说:“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里面风是阴风,气是邪气,每个眼神都透着的杀机。时而那凄惨的尖叫声,打骂声,一个月后,我三十岁的人看上去六十岁了。精神的压力有时超过身体的承受千万倍。
而丈夫在家找遍公安局、派出所、乡政府、市政府,找不到人,谁也不告诉他我的下落,一个月后他才托人打听到一点线索,而公安局还推脱说不知。最后丈夫顺一点线索找到王村要人。临放人前曲秀英把我换到一个不知什么房间,逼我骂师父写“三书”(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否则判我如何,僵持了一上午。她象疯了一样把她写好的东西拿在我手里,强按手印才放我出来。这里我再一次声明那一切作废。
我一个月的经历老化到六十岁!而那一年、两年、三年的白天逼那些人干活,晚上还得写“三书”(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每日如此。那样的压力下,也有时不时地有人站出来否定自己的违心言论,结果是酷刑折磨。我因为本来就全身多处碎了,受不了酷刑,劳教所才不得已放人。
上千名法轮功学员都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无法用笔墨充份表达出来迫害之惨。望国内外良知人士正义声援,制止迫害!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html/articles/2010/9/9/1199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