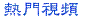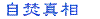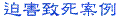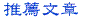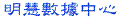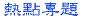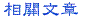我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受的种种残忍迫害
一、奴役
在做奴役的过程中,因为天天接触制作祭奠死人用品的乳白胶(乳白胶中含有毒性物质,会导致过敏、气管痉挛、哮喘等症状),导致我血压高压160低压100,痰中带血,呼吸困难,有明显的过敏哮喘的症状,11月我被转入和普教在一起的一大队。
我到车间后,看到到处都是堆积的棉大衣,人人都紧张的忙着手里的活。不时传来带工(普教代队长管理生产及内务的)破口大骂声,稍不如意,举手就打,环境十分恶劣。队长们则聚在一起吃着水果、嗑着瓜子说笑(各种水果、饮料、小食品都是普教带工孝敬的)。如果有谁稍不服从带工管理,队长再去骂或者是打。
每一次干新活,刚开始给你2~3天适应,以后每天工作量都在递增,大部份人根本都无法完成。完不成的轻则被骂、被罚站,重则被扇脸,被电击。打完之后回来还得继续干,还干不完就得加班干。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叫王娜的普教加了一夜的班,早上还得照常上工。
记得2007年12月下旬,一大队、二大队疯狂的加班,每天都干15~16个小时。又脏又累,伙食又特别差,没有一点油水,有时就是一碗飘着几根菜叶的清汤。直到有一天晚上10点半钟左右获得消息的记者突然闯进了车间,对着车间拍照,又随机采访了正在加班的人,正好采访的是法轮功学员。警察们都傻了眼,当即宣布收工。从那天起晚上不再加班。这样,他们只能在别的地方做手脚,如延长收工时间,把活拿到号里干等等。
二、“扣扣抻”
转眼到月末签考核的日子,为抵制无理迫害,法轮功学员都不在考核表上签名。我当时坚决拒绝签字,并跟队长讲真相。后被大队长张春光带到东港(以前用于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后来人员减少,被专门用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小号,里面有酷刑大挂、电棍等等)上刑。
张春光首先把我铐在房间两侧的铁床中间,双手被抻成一字型。当时正是大冬天,我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三个小时。后来又进来了7个警察,张春光、李明玉、周谦、翟艳辉、陈秋梅 等妄图对我加重迫害。我奋力的抵抗,最后他们将我双手分别一上一下的铐在两张铁床中间(一只手铐在铁床的上铺,另一只手铐在对侧铁床的下铺),其中一侧床上面压了很重的东西。他们用脚使劲踹,把对侧的床踹到踹不动为止,这时手铐已深深的卡在我的肉里。这就是马三家的“扣扣抻”。
我痛的撕心裂肺,大汗淋漓,人几乎昏死过去。很快手和手腕发紫,这样持续了16个小时。中间他们不时的进来踹床,使劲的晃动本来就已经十分剧痛的手。下来后双手肿的像馒头,有16处皮肤磨破。
三、莫名其妙的“化验”
2008年5月12日我又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的抽血迫害。这天,警察们不做任何解释,要求每个人抽一管血说是化验,至于化验什么以及检查结果根本不告诉我们。
当时我坚决抵制抽血并大声讲真相。最后管教科的科长王延平还有另外2名警察来拽我。我死死的把住门不松手。这时又上来大队长李明玉,干事翟艳辉以及马三家医院来抽血的警察共九人。我坚决不配合他们,他们拽我十分吃力,无法在抽血室抽血。他们只能就近把我推到对面的一个房间,我高喊:“法轮大法好!迫害法轮功学员有罪!”他们非常害怕,就让所有的人立即到楼外面站着。
他们把我拖上床,王延平压着我的头,李明玉摁着我的胳膊,另外还有人压着我的身体和腿,并把我的双脚压在床栏下。我仍高声喊:“法轮大法好!不许迫害法轮功学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且用尽全身力气反抗,他们扎了一针没扎上。这时王延平顺手从床上抓起一个枕头,压在我的脸上。瞬间我感觉无法呼吸,这时我的头碰到左边的墙壁,我立即把头用力的往墙边靠,借助脸部和墙之间仅有的一点点空隙呼吸,才使我免于窒息死亡。
四、强行乱用药物
在马三家还有一种无视生命的做法,在这里的警察可以随意的使用内科抢救药救心丸。此药的适应症是心绞痛、气滞血瘀型冠心病,一次4~6粒,急性发作时10~15粒。我在马三家非法关押期间,在心脏很正常的情况下被警察强制的使用了2次救心丸。
第一次是07年的11月15日,当时我被上扣扣抻,被迫害的呼吸困难,大队长张春光强行让我吃了7粒,我很快就吐了出来。这药药效十分迅速,只有几分钟我血压就下降40,浑身抽搐不停,蹲在地上。
第二次在2008年10月7日那天被强行灌了9粒救心丸。那天一大队的法轮功学员集体抵制签考核,在李明玉和张春光的主使下,蓄谋已久的管教科男恶警5~6人,其中有彭涛、张良……把法轮功学员一个个的点名往外拖。法轮功学员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恶警们上来就拳打脚踢,随后拖至东港折磨。有的扇脸,有的被电击,有的被铐。每往外拖人时,大伙就高喊:“法轮大法好!”恶警冲入房间挨个打,我们照样喊,这样持续了3个小时。最后我被叫到队长办公室,我仍然拒绝签字。这时恶警赵国荣拿着电棍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电棍啪啪的放着蓝光。最后彭涛、张良把我的左手扭到后背,像小燕飞机一样,另一只手被按着签字,我坚决不签,他们两次强签都没签成。最后又上来2个女警一起把我往东港拖,他们一边拖,我一边喊:“法轮大法好!”
东港里面已经铐了五名法轮功学员。他们把我的双手用手铐死死卡住,各绑一条布带,两个男恶警把我拖到一张上下铁床的床头,把我的双上肢和整个上半身从上下铺中间拽到了床尾三分之二处,再将我的双手抻紧绑在上铺床尾横梁的两头(上这种刑时,身体弓着,头抬不起来,身体全部重量都压在双上肢及手腕处)。
立刻,钻心的剧痛使我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完全象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什么样,但警察却立即叫来了卫生所护士项某某强行灌食救心丸。我紧闭嘴唇,她灌不进去就左右开弓扇我脸,最后这个恶警护士一手捏着我的鼻子,一手扇我的脸,在我憋得上不来气的情况下,她把药塞进了我的嘴里。
当时管教科的王延平(现在是一大队的大队长)一边揪着我的头发扇我的脸,一边阴阳怪气地说:“你还给我上明慧网。”听到明慧网,彭涛立即漏出凶相,也过来扇我的脸并说:“你还上明慧网”,此时我的脚下已经落了一地的头发。这时又来了一个警察捏着我的鼻子又要给我灌救心丸,不知谁在旁边喊了一声:“别灌了,刚刚灌了9粒了。”这个警察说:“真玄啊!我又拿了9粒。”
后来我又看到了好多起这种乱用药的情况,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个警察,甚至带工的普教都可以从箱子里随意拿药往人嘴里塞。
当晚8点多钟,大家到东港拿行李(大家的行李都是早上送过去,晚上再拿回号里,平时号里摆的都是应付检查,给外人看的行李)。法轮功学员卢林喊“法轮大法好”,我随即也喊起来。李明玉、张春光慌了手脚,立即找来宽胶带在我的头上绕了好几圈,这样口鼻都被封在胶带里。就这样过了12个小时,当胶带被撕下时,扯下来的头发加上被恶警揪下来的头发,我脚下一米见方的地方几乎盖满了头发。在此过程中,女二所所长杨建三次督阵,他每次来张春光都把我的手铐紧了再紧。这种痛苦用尽人间语言都无法形容,就这样我被抻了23个小时。下来时,我的双手已经没了知觉,黑紫色的手上布满了水泡和破了皮的肉,共有23处外伤,惨不忍睹。
以后的几个月我连饭碗都拿不住,尤其是左上臂内侧被翟艳辉上大挂时用脚踢在腋窝下完整的一个黑黑的脚印,很长一段时间皮下淤血才消失。以后双手功能严重障碍,双上肢肌肉萎缩。我几次找张春光、李明玉、陈秋梅提出要上医院做医疗鉴定,他们每次都答应却始终一拖再拖。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他们找来了马三家卫生所的一个大夫,午休时隔着铁门看了看。当时我的双手明显畸形,虎口肌肉萎缩,双上肢肌肉萎缩,胳膊变细。卫生所的大夫问我以前手有没有毛病,我回答是前些日子上大挂时被抻的。张春光听后吓的变了脸,没等大夫做检查,就说:“好了,好了,今天就这样吧。”当时我很纳闷,原来即使马三家的警察之间也是互相隐瞒的。后来直到我离开时也没有人领我去检查过。
至今二十个月过去了,我仍然左手麻木,双手指根部仍见肿状。
五、乱收费
在这里被关押的人员没有一点人权。在生活方面,教养院的食品本来卖的就很贵,大伙买的食品,大队长尤然今天让放这,明天又改了。原来放的位置全视为不合格,统统没收。我们找她要的时候,她就说没有了,全扔了。找到她主管大队长王延平时,她说:“不知道,别来找我。”她们就这样推来推去。一个月下来不知道折腾了多少次,很多人的东西都被没收过。私人放的衣服柜,自己有一把钥匙,尤然有一把钥匙,她随时随地的去翻柜。经常早上放的好好的,晚上被扔了一地,她只是说翻号了,去收拾吧。每一次都有日用品和衣物丢失,问谁谁也不知道,一点保障也没有。
教养院还乱收费,本来国家拨款的设施都要大伙分摊。一个300多元的晾衣架不知被重复收了多少遍钱,至今新来的人还要交这笔钱。自己买的水杯、脸盆、衣服,走时还要上缴,再卖给后来的人。这里有艾滋病人(我在期间有2个),有肺结核等传染病人,却没有任何防传染的措施。如果有人找王延平和尤然提意见,他们就说:“闭上你的臭嘴,臭不要脸”等侮辱人格的话。
以上我所经历的只是罪恶的马三家迫害的冰山一角。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html/articles/2010/7/19/1186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