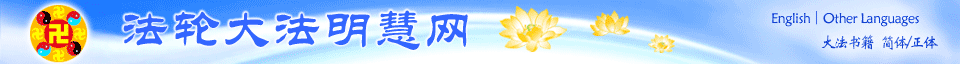【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一月六日】我今年七十六岁,九七年一月得法。得法前我多种疾病缠身,严重的有萎缩性胃炎、关节炎、气胸病、神经衰弱等。得法炼功后师父都给净化了。记的最严重的一次消业长达四十多天,脖子上鼓起了一个鸡蛋大的包,喘气非常困难,说不出话,发声很困难,吃饭也只能喝一点稀的。儿子(未修炼法轮功)硬逼着我到医院,二女儿也对我老伴施加压力(因为是老伴带我進的大法的门):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的就跟他没完!我和老伴都没有动心,只是笑着对他们说:这是师父在给消业、净化身体,不是病,不会有事的。就这样,四十多天闯过了病业关。从那时起,所有的顽疾在不知不觉中被彻底清除,体重也逐渐增加了,每天精力充沛,走路一身轻。
九九年“七·二零”之后,我是我们乡镇第一个和城里的大法弟子结伴一起到北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的。当时我们乡镇的其他大法弟子看到我这么一个老太太也到北京,非常震动。后来就三五个结伴都去了北京。结果乡镇的邪党干部和公务员都象炸了锅一样乱了套,非常紧张。把我和全乡镇去北京上访的大法弟子都关在一个冰冷的大礼堂里将近一个月,不分昼夜的看着。一天乡镇邪党干部和公安派出所的恶警手提电棍、大棒子像一群恶狼一样突然冲進了礼堂,二话不说对着被关押的大法弟子就开始狂电、暴打。我当时就哭了,大声喊着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打人!?我们犯了什么法!?”当时他们就被震住了,停止了暴行。后来,他们穷凶极恶的使用了各种恶毒的招法迫害这些大法弟子,包括强行灌酒等。
最后,我们每人要被迫交纳五千元“罚款”才肯放人。因为我们家得法比较早,老伴又是辅导员,我又是第一个去了北京。邪恶们认为是我“号召”、“串联”、“组织”别的大法弟子去的,所以对我非常重视。老伴在家里也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压力,就被他们敲诈勒索去了五千元钱。
回到家后,面对各种家庭的压力,我没有动摇证实大法的决心。之后我就开始自己制作“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条幅,晚上就顶着寒风、甚至踩着积雪到马路上往树上挂;抽空和老伴提着油漆在电线杆上写各种证实法的标语,让世人知道大法的真相,知道我们的心声。这期间,邪党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还经常進家骚扰、恐吓。后来又把老伴绑架到当地邪恶的“六一零”关押、迫害了四十多天,直到我让我儿子和女婿去要,他们才不得不放人。
之后我们于零一年全家搬到了县城里居住。我们就开始不断的讲真相、发放资料。有时候在所谓“敏感时期”、“风声很紧”的情况下,怕心也不免会暴露出来。我便背着“大法不离身 心存真善忍 世间大罗汉 神鬼惧十分”(《洪吟》〈威德〉)的诗句走出家门,继续证实法。这样风风雨雨中我从不间断的发放着各种真相资料,张贴各种真相标语。走到哪里就把大法的美好带到哪里。后来《九评》、神韵晚会及真相护身符的发放也及时的让世人明白了真相,看清了邪党的真实面目。几年中我还利用各种喜事宴席等回到老家讲真相,劝退了村里的大部份党员。我家的所有亲戚朋友也都大部份做了三退。
另外,在这近十年的时间里,我和老伴一直和老家的同修保持联系,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我们都及时把师父的讲法、经文及周刊、资料传送过去,从不间断。总之,这几年我们在信师信法的路上平稳的走了过来。
零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老伴突然以睡觉的形式先去了,这件事情造成的家庭压力也很大。但我内心没有丝毫的波动,除了深深的遗憾。老伴曾经因心脏病的形式于零五年去过医院、做过心脏支架,但回来后不断学法,心也慢慢放下了,也不吃补品了,三件事也做的很好。但就是在零九年过年的一段时间,家里来的客人较多,同事、朋友常来找他聊天,他又放松了学法,发正念也常常受干扰,没有及时补上。而我没有及时从法上帮助他补上,而只是埋怨、责怪。旧势力抓住把柄无情的让他先走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歉疚,也留下了太大的遗憾,更让我明白了修炼的严肃性。同时这件事也激励着我和其他同修抓紧做好三件事,因为这不光是原定天年、旧势力干扰的问题,还有救度众生的急迫问题,我们只能更抓紧,不能有丝毫懈怠。在回老家安葬老伴的三天中,我又劝退了好几个人。回来后我继续按师尊的要求更加抓紧做三件事,以免再留遗憾。
以上是自己这十年来在证实法的路上的一些经历和体会,所做的离法的标准还差的很远,做的还远远不够,因为还有许多人需要我们去抓紧“抢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