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十八年
九月十三号,我一家人都参加了师父在重庆办的讲法班。九堂课听完后,认识到这个功法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气功,是能使人道德回升,又能使人修炼返回去的高德大法,而且这么短时间就受益良多,觉得这就是我一生中都在寻找的,终于找到了,这下我的人生有希望了,要一修到底。那时不知为什么,在潜意识中好象预感到最后可能会有一个想象不到什么方式的考验,我下决心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都要坚定的修过去。
虽然十几年过去了,但参加师父讲法班的点点滴滴都留在我的记忆中。
记得有一次师父走下讲台纠正我们动作的时候,有一个同修的小女孩六岁左右,师父在小孩额头的天目位置上点一下,指着台上矿泉水的瓶子,问小孩:“看得见不?什么颜色?”小孩说是蓝色的。可我们却看到都是透明的。
还有一次,我们排队等着师父在《中国法轮功》(后更名为《法轮功》)书上签字,我丈夫拿自己的笔让我给师父,请师父给签字。我说,老师,用我这个签吧。师父笑眯眯的说:“不用,用我这个吧,我这个威力大。”
一九九四年五月,我有幸第二次参加了师父在重庆三钢电影院办的讲法班。有一次准备進学习班听课时,远远看见师父走过来,穿一件衬衫,黑裤,凉鞋,很朴素,仪表堂堂,感觉师父很高大,这珍贵的一幕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了。
我们一家人和师父照过像。这张珍贵的照片还一直珍藏着。邪恶抄过几次家了,都没有被他们发现。
得法前一身是病,炼功后一身轻。以前有过:白血球减少,血小板减少,胆囊炎,低血压,低血糖,荨麻疹,喉部严重的肥厚性水肿,整个喉头被炎症包围,声带炎,说话声音嘶哑,低八度长达十年,因以前爱唱歌,很痛苦!心跳过缓每分钟四十多下,整天就是累,没有劲,看见人笑不出来,说话总是冒火,别人说我脾气不好,不好接近,中药、西药吃了一大堆,断不了根,病情反复发作。
炼功后变成另外一个人,无病一身轻,性格也开朗了。单位里不炼功的常人说,你们这功真好,经常拿我做例子,以前碰到就炸,你看现在她多好,所有的病都没有了,这功法真神奇呀!
为了准时参加集体学法,我下了班就直奔学法点,学完法再回家做饭吃,都接近晚上十点了。也经常出去洪法,最远的去过西藏,都是自费去,回来后晒得象个黑炭头,就觉得这个法好,想让更多的人受益。每天感觉过的很充实,很快乐。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恶从天而降,在迫害中,被非法劳教一次,被关進洗脑班三次,被非法拘留一次,正念抵制两次邪恶迫害,也遭受过各种酷刑。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我闯过了一关又一关,下面将我这十九年证实法的路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
大法书被保护下来了
一九九九年八月居委会通知交出所有的大法书,熟悉的几个同修商量第二天去交书。某同修说看来不交还不行。当时我说了一句《转法轮》也要交吗!?她们没吭声。第二天她们说,昨天晚上书已交了,我当时思想中就没有要交书的念头,倒是想过,真的逼紧了,就把心得体会交了算了(这一念也不对),当听到她们把书已交了时,我和她们说,你们已经交了,那我一个字也不交。有了这一念,过后没有任何人再叫我交书。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四日,我准备進京上访为大法讨个公道,在当地火车站被劫持。当时还有点不知所措,因从未经历过。同修们都互相鼓励,背诵:“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洪吟》〈无存〉),也背《论语》等经文。
警察把非法劫持的同修们送往各派出所。到派出所首先搜身,把衣服解开。九月份在当地穿衬衫,同修放包里的大法书《转法轮》都被搜走了。我就想:师父呀,书不能让他们抢去。我有两本《转法轮》,一本大的,一本微缩版,该怎么办哪?放在包里也要搜,放在哪里都不合适……突然师父的法一下闪在脑海里:“大法不离身 心存真善忍 世间大罗汉 神鬼惧十分 ”(《洪吟》〈威德〉)。师父点化放在身上是最安全的,我就把书插在腰上,因我的腰比较细,看不太出来。到检查我的时候,邪恶从裤子口袋里搜出电话本看了一下,又还给我了,在师父的呵护下邪恶想不起搜我的身,闯过了一关。
在派出所连续十六个小时不让去厕所,很难受。两天后在宾馆关了一夜,看守很严,我看到一同修的儿子来了,马上想到把书转移出去,用尼龙袋把书包好,大步往门外冲,转弯处将书迅速交给同修儿子让他交给我家人,书终于安全送出去了。
每当考验来的时候,总感觉到师父时时就在身边看着,帮助我一样。
正念闯出洗脑班
第二天把我们其中六个人送洗脑班。在洗脑班里,我们不配合邪恶,坚持炼功打坐,讲真相证实大法。有一个二十几岁的男大学生准备来给我们洗脑,我们就给他讲真相,背《论语》。他赶快把门关上,说:“你们老师讲的是有道理。”他一直听完我们讲的,知道了大法是教我们做好人。就这样大法又救了一个生命。
有一天晚上,几个值班的悄声说:改变她们很难。最后几天由公安局副局长坐镇审问。進去一个就谈一、两个小时,最后问还去不去北京?回答:去!炼不炼法轮功?回答:炼!问一男同修要党员,还是要法轮功?两样只能选一样。男同修说:要法轮功。这个男同修得法前是晚期鼻癌,经常流鼻血,修炼后就好了,大法救了他一命,他能不炼吗?还有一个同修不管他问什么,都是一个回答:“法轮大法好!”
整个洗脑班十五个同修,十四个都坚定的正念闯过了这一关,只有一个小男孩不炼了。
魔窟中闯过一关又一关
二零零一年四月三日,我到亲戚家讲真相,在那个地区张贴真相帖,被恶人举报。四月五日,恶警闯到我家中把我绑架。我被非法劳教两年,退休金扣发了一年多。开始被关在“人和女子劳教所”,半年后,劫持到“茅家山女子劳教所”(现称“重庆女子劳教所”)继续迫害。在茅家山劳教所迫害更为残酷。
我那时不管到哪里都觉得师父就在身边,不管到哪都不忘讲法轮功的美好,即使在被迫害的魔窟中也不忘讲真相。在两个所都有有缘人听到我讲的真相后对大法有了认同。其中有犯人也有狱警,那时还没有“三退”的做法。
在劳教所,我不穿囚服,恶警威胁我,最后问我,到底穿不穿?我想到任何时候都要把大法放在首位,就回答:我不穿!这时恶警反倒不说什么了。
有一天邪恶骗我,问我愿不愿意和同修交流,我说愿意呀,他们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当时我还很高兴。一见面就急切的说要坚定的修下去等。可她们却自豪的说她们進来一个星期就“转化”了,我一下子明白了,她们都是邪悟者,要来“转化”我,我一下脸就拉下来了。我请师父加持弟子一分钟也不想在这里呆,四十八小时后把我带回原来的地方。自那以后,恶警没再叫邪悟者“转化”我。由于信师信法我又闯过了一关。
有一次司法局的一男一女找我“个别谈话”,我一進门就对他们说:你们是不是来“转化”我的,要“转化”我就不要来,我是不会被你们“转化”的。他们赶紧说,我们是来摆家常的。我说摆家常可以,我就让他们给我家人带话,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们说我丈夫上午去找过他们,说他已有半年多没见到我了。所以他们来看看我的情况。最后听到他们私下说,我们是来“转化”她的,她反而让我们带法轮功的话。
在魔窟,不仅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在肉体上更受着惨无人道的迫害。
二零零二年三月,从西山坪调来了很多男劳教所的恶警配合女子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他们互相交流迫害经验以达到其迫害目地(莫水金大姐就是在茅家山劳教所被迫害死的)。
曾经有一次以军训体罚法轮功学员。我不配合,拒绝参加。劳教犯人就来抓我的脸,抓的我血流满面。我还是不配合,他们就给我上铐,罚站三天三夜不让睡觉。第四天早上我横下一条心对旁边的犯人说:今天打死我我都不站!觉得师父就在身旁看护着我。犯人去找恶警队长报告,回来一声没吭。我又闯过了一关。
不让大法弟子睡觉,逼站“军姿”,逼唱邪党红歌,长期坐小凳,捆绑,等等是常有的事。到我快出来的最后一个月,也就是二零零二年五月,那时迫害达到高峰,所有不配合邪恶的大法弟子天天挨打,每天军训若干次,从四楼到操场来回不断折腾我们,动作稍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就得挨打,打肩头,打得连手都抬不起来了。男恶警上来就拳打脚踢,很多大法弟子被这帮男恶警打得浑身伤痕累累。
我在那里曾经遭受过惨无人道的人身侮辱,有一次邪恶对坚定的大法弟子進行所谓的“搜身”,衣服裤子都脱光了……,我觉得对于女性来说,这简直太没有人性,至今多少年过去了,我写到这里仍然会掉泪……
有一次一个武姓的恶警大队长非法审问我,我就先发正念,她表现出的好象累得连站都站不住,累得不行,就发脾气,后来又不知谁告诉她,我在发正念(这说明正念是有威力的,一定要相信正念的作用)。
有一天晚上,每个房间都被叫出去一、二名大法弟子,在不同的房间审问,我是其中一个。由一个女犯包夹,房间里象设公堂一样,三个男恶警坐一排,还有恶大队长武××。还有一名高个女犯人,象个粗野男打手一样。那时我身体很弱,很瘦,但头脑很清醒,觉得师父随时都在我身边。
他们叫我跪下,我不跪。他们在我的背上就是几拳,强迫我跪下去。女犯抓住我的头发,使劲往地上拽,当时气都喘不过来,但头脑很清醒,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说:“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心里叫师父:师父啊,不管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妥协、‘转化’,强制改变不了我对法坚如磐石的心。”那高个女犯在打完我之后,我转过头正视她,那女犯看到我,低声说:“我看你的眼好害怕。”这就是正念的威力。
中间过程很多,审讯的话也多,就不细说了。一想到师父,我的正念就越强。男恶警问:“还炼不炼?”“炼!”最后问我有什么感想、体会,我没有理他。旁边的女犯又说:你说什么都可以,一下悟到师父借犯人的嘴点化我,我就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那个高个女犯低声说,“爽快,有胆识。”偷偷对我竖起大拇指。
邪恶在记录上叫我签字,因当时被打的手也抬不起,背也伸不直,哈着腰走。拿起笔甩了一下手,因手抬不起来,我也有意让邪恶知道:你们迫害了我。我写上“法轮大法好!”签名:大法弟子!写完放下笔,感觉一身轻。带头的男恶警说,今天足够判你的刑。你们不要打她了,不然你们都把德给她了,把她拖回去。气得那头把口供撕了。
走出门外有认识我的女犯人,因我换了好几个号房,有很多都认识,都向我示意,我给她们也讲过真相。
高个女犯说:阿姨对不起,我不打不行,是他们安排的,不然要加刑。
二零零二年五月,从其它监区调来了很多吸毒犯,所谓的“加强管理”,每监增加好多个犯人,晚上连地上都睡满了。五月十八号正集合准备吃午饭,也不知道是啥事又把我叫出去。那时我走路直打晃,一边走一边用手提着裤腰,因瘦得皮包骨头(腰一尺六),脱了人相,衣服大,裤腰也大。
走到大门边的接见室一看,丈夫来接见,我问领路的队长,我可以把里边的情况给家人说吗?那队长当时象什么也想不起来,立即说可以呀!说什么都可以。这都是师父安排,我就把里边包夹我的犯人打我的经过和身上的伤,头部撞的包让家人、队长看,她说谁打的,我说不是你们叫犯人打的吗?她说哪里会呀。我说被劫持進来体检时我血压就偏高,现在又被打成这样,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家人强烈要求送大医院全面检查,当时狱医就来量血压,我立即发正念:你的血压表不好使,我的一切由我师父安排,量了两次,低压一百六十二高压二百四十二,她俩对视了一下,立即叫我出去。他们商量一下,让我回监号,休息,想坐就坐,想睡就睡,什么也不要想,还可以在走廊上走一走,我利用这些机会不停的发正念。邪恶召集包夹我的犯人谈话,说出了事要她们负责。又假惺惺的叫一名大法弟子去问是不是被打过:是!从那天开始听不到打人的声音。因邪恶觉得我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怕我死里边,因家人看到我全身都是伤,特别是背部全是紫色,也在找它们说理。
第二天,我被送到当地大医院检查后,又送回劳教所,检查的所谓病情不告诉我,就是天天叫我吃三次药,天天叫犯人给我热敷有伤的地方。它们害怕罪证被曝光。天天量血压都是不正常,我也在天天发正念。邪恶不放我,拖延时间就是想掩盖罪证,也随时来假关心。我说你们叫我休息,你那高音喇叭放的是什么,我怎么休息,我的脚也麻了,头也麻了,我要出去,要回家。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我清静不下来。从那以后高音喇叭停止了,什么都静下来了,有时犯人陪着我放风,我留意观察同修的近况,每道门都关的严严实实的,过道上没有人,只有值班的。突然一扇窗开了,我抬头一看,几个同修面向墙罚站,听说都站几天了,知道了这个迫害一点都没有减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采取面壁罚站,不让睡觉。
在走廊上碰到一个同监室的刚被“转化”了的同修,准备把她调到一大队去。一般转化了的就往一大队送。她对我说:“你也快点“转化”吧,我看了新经文,师父不管我们了,自己逃命吧。象我这样就轻松了。”我一听就知道是假经文,我知道师父从来不会不管我们的。旁边看着我的警察指着我说:“她才不会‘转化’呢!”
因血压高,邪恶天天逼我吃药,每天三次,还要张嘴检查,但它们不敢动手怕出事。我巧妙的用智慧度过了难熬的这十天,吃的药一粒没進肚子。十天后,厂公安分局负责人和家人来接我回家,问:你怎么这个样子了?我说是它们打的。另一个负责人说,共产党的监狱哪有不打人的哟。下车后他俩跟我家人说回去好好照顾她,她很严重(指病)。
自己没有动念,也没在意,这一念之差就有不同的结果。第二天劳教所一知情人打电话给我家人说:她很严重,当时医院医生要求立即住院,很危险,严重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我知道了也没有在意。似听非听的,不知怎么就是不当回事,脑子里打不進去“病”的概念。只是感觉有点疲劳,累,但都没有去多想,就是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后来听家人说那时背也弯了,头发也白了,象个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认不出来了,那时我才五十来岁。
在师父慈悲的加持、呵护下,正念闯过一关又一关,最后以“病”业的形式,提前十个月闯出了非法关押迫害我的魔窟。
正念对待各方面的压力和干扰
闯出魔窟后,家人觉得我好象也就只能活三天了(恢复后家人说的),就要带我到医院检查。我说不去,我要炼功。丈夫说不行,要去医院。我说那你就把我送回劳教所去吧,我什么都放下了。过一天我又对他说,你刚才不在家,我打坐了十五分钟,身体舒服多了。他说那你就炼吧!
经历了很多家庭关,只要在法上去认识法,相信师父,坚定在法中,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在这个过程中悟到,自己修炼的提高的过程,是放下人的观念的过程。人的观念不放,神的一面就展现不出来。
这其中还有儿子、媳妇的工作问题,孙女的学习问题等等,只要把人心放下,什么都能安排的很好。仅举一例:儿子原先在汽车高工位流水线工作,一天下来,累得不得了,脚跟不能着地,想换工种,要我去找人,我知道这是冲我来的,就是要我放下对儿子的情,我问儿子:“会不会死人?”儿子说:“那倒不会。”“那我们就把这颗心放下,放不下就改变不了。”过了几个月,儿子被安排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岗位。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三日,下午六、七点钟,我从外面刚回到家,就有人按门铃,从猫眼看不到人,就以为儿子下班回来了。一开门闯進来七、八个恶警,拿着手机,挂着照像机,拦都拦不住,气势汹汹的闯進来。我说既然進来了就坐吧!第一念想到的就是:师父,今天我不能跟他们走。盘问多时,不正面回答,就讲真相,发正念。又问认不认识谁谁?我一听到姓名,就明白我被出卖了。
在主卧房,邪恶叫我打开抽屉和衣柜,我说没有你们要找的东西,不开。邪恶自己打开抽屉,乱翻一气,东西扔了一地,找到一本《转法轮》,一盘炼功带,我说你们不能拿走,那是我丈夫的。邪恶说不行,于是我丈夫立即从他们手中抢过来,说:这是我的,我拿钱买的。磁带是我找别人给我录的,谁也别想拿走。本来邪恶迫害就不敢见光,邪恶就真不敢拿走。其实我房里(我和丈夫分房住)有刚从外地拿回的一大包光盘等资料。放在床上还没来得及收呢。我的抽屉里什么都有,可我就是心不动,我看都不看放东西的地方,邪恶象是想不起来,就在其它地方乱转,房顶、床下到处看,没有找到一张他们要找的资料。最后,底气不足的说:“跟我们走,还要做个笔录。”我说:“大人、小孩都没有吃饭,我要做饭,我不去!”邪恶看没招了,只好说,你明天到公安局来一趟。一定要来做个笔录。我当时就想,我才不上你们的圈套呢,去了就回不来了。当天晚上不停的发正念,清理资料,早晨趁天还没亮,出去把整理好的资料发了。当天亲戚打电话叫我离开,才想起来该离开了。在师父的点化,呵护下,化险为夷,闯过这一劫。
拖着一个病的不能自理的丈夫,到亲戚家附近租了房子。自那被迫离家出走至今。晚上趁丈夫睡觉写真相币,给邪恶寄真相信,等到晚上半夜,丈夫睡着了,就出去张贴真相帖,发放资料等。
这期间,邪恶到处找我,找不到。
抓紧时间救人
利用回老家机会救人
二零零三年丈夫胆结石复发,正准备手术时,又突然转危为安,想到是师父在帮我,师父在点化我,没事赶快抓紧时间去救人吧!正好女婿有事去北京路过我丈夫的老家,女婿就借机会了了老岳父总想回老家的心愿。
回老家后,通过讲真相,使四、五家人明白了真相,生命得到了救度。特别是表弟媳,陪我们转了一天清东陵。里面很大,乘汽车都要转一天才行。她说以前一直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今天怎么精神这么好,一点不累,笑逐颜开。我说相信了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师父在管你。她激动的说:“我信!”看得出是出自于内心的信。
回过头来又到北京对亲戚讲真相,近距离正念。发一念:清除北京所有烂鬼!后又转石家庄向亲戚、同学讲真相,一般都接受真相。
在石家庄,与几家亲戚讲完真相准备上火车时,遭到个别亲戚的举报,明真相的亲戚鼎力相助,在师父的加持中,拖着丈夫赶路,并不停的发正念。那时开始检票,亲戚急来告之,灵机一动,买了两张站台票,顺利的上了火车,拖着一个痴痴呆呆走路都不灵活的丈夫正念走脱。真的是火车站“化险为夷”,这个过程现在说起来轻轻松松,当时真的是惊心动魄,当时站台上警察都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显然这都是假相。
二零零七年一位老同修的弟媳在北京去世了,我要去一趟,同时给她那里的亲属讲真相。在这之前因老家亲戚还有没做“三退”的,也曾动过一念,想再次去北京救人。但也有干扰:当时丈夫留下脑溢血后遗症,行动不便,脾气也怪,儿女都怕他,不愿接受他,我若出去必须带上他,而他当时不愿去,我毫不犹豫的问:你去不去,他说不去,那我就订一张票。他看我真去,就说也要去,订了两张机票马上就走。救人急,脑子是空的,只有一个念头能让我走怎么都行,也是一粒药也没带,也想不起来,他也不说。就想着救人,觉得很多事都是随心所愿,都是师父在安排,自己哪里做的了啊。
到北京的当天晚上把弟媳老家亲戚基本上都做了“三退”,也讲了真相。第二天一早在八宝山也抓紧时间救人:遗体告别仪式完了就抓紧切入主题劝“三退”,退了好几个,三位从法国回来的亲戚温文尔雅,说话亲切,他们明白真相后也都退了。
这一趟总共退了几十人。
老同修弟弟说:你们怎么不去参观某某等名人的墓碑,好漂亮。我们只是笑,想的只是救人,对其它一点兴趣都没有,沿途又去了唐山,贴真相标语,顺利的给五家亲戚做了三退。表面我们在做,其实都是师父在安排,加持着我们去做表面的。众生都在等着得救啊!
返回北京近距离发正念,总之走到哪里正念都不停。最后到石家庄做完三家亲戚及丈夫几个同学的“三退”顺利回家。
利用丈夫住院期间,救度有缘人
一次,丈夫突发脑溢血,我从外地赶回家,张罗着让丈夫住上医院。因我从劳教所刚出来身体消瘦,恢复阶段在外地女儿家住。在丈夫住院期间不忘讲真相救人,退了几十人。又跟丈夫讲,让他默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CT检查结果,脑血栓没有了,医生说这是奇迹,一个月就出院了。这以后每年都要住一次医院,我也利用这个机会让有缘人得救。
二零零九年,在异地丈夫脑溢血复发,全身瘫痪,失去了语言能力。住了医院,做了手术,还算成功。心里明白,我应该利用这个环境,利用丈夫在异地的住院安排讲真相劝“三退”救人。因二十四小时都在输液,又要吸痰,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为了讲真相机会多一点,时间宽裕些,请了一个护工每天工资一百二十元,当时我们俩的工资加起还不够付护工的钱,而且每天医疗费就三千多元,但想到能有时间做救人的事就一切都放下了。舍钱才能有时间救人。关键时候就看以什么为重。钱可以想办法,救人机缘错过损失就大了。
救人过程中出现过几次奇迹。例如,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凌晨,有一名七窍流血的男青年被送来脑科抢救,床位紧张,临时在走廊上安了床。等着他的亲人来办理手续,二十四号晚上他弟赶来了,说是第二天照CT准备手术,可能颅内有积血。他弟急得团团转,我主动与他说话,我以第三者的身份告诉他弟弟大法真相,当时他就退了团队。他不想让他哥做手术,担心有后遗症。当时他哥处于半迷糊状态,不说话。我告诉他弟让他哥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他哥开始有点清醒了。他父亲也从湖南赶来,我就劝他父亲和他一块念,其间我每天都发好几次正念,清场。一家三口都作了“三退”(父亲是党员)。他弟说只要我哥没做手术病好了,我就要告诉别人是法轮功救了我哥。
最后一次CT检查后,他弟告诉我:现在一切正常了,不知怎么一下子脑子里的出血就没有了,医生也觉得是奇迹。弟弟很感激的说:“感谢大法师父!谢谢阿姨!”我说不用谢我,是我师父要救你们全家,通过这种形式安排,我们才有缘相见,你有缘听真相。一个月后这个病人就出院回湖南老家了。
很大一部份人我都是理智的用第三者身份劝“三退”,用智慧编成故事讲效果很好。
丈夫二零一零年三月七日,假死过一次,医生都认为他马上就断气,儿子、媳妇请了丧假,当晚乘飞机赶回来,呼吸机也拔了,氧气也停了。儿子和我不停在耳边跟他说:走到哪里都要记住回家的路,“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没想到,十几个小时后,把痰吸了,他又活过来了。医生说他生命力很强,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
这个地方属于中等城市,城区路况不好,车祸特别多。重伤多,死亡多。因这是脑外科,来了一批又一批。还有众生要来这里得救。我就继续给来医院的病人家属讲真相。丈夫活过来后我又劝退了七、八十人。这次丈夫住院期间,我前后给三百来人做了“三退”。我是脑科住院部公认的好人,别的病人拉屎拉尿等,我都主动帮助。
六月底医生说我丈夫现在是最好状态,可以回家了,他的时间不会太长。女儿怕他死在外地,可我是因反迫害长期在外,两难。女儿问我怎样决定?我说:回去。悟到师父借医生的嘴点化我们该回去了。二零一零年七月三日我们乘火车顺利回到家。我发出一念:谁也看不见我,谁也不配来迫害我,请师父加持。
七个月后,二零一一年的大年初三,丈夫去世。一般人死亡,派出所、居委会要来家里签字证明,是否正常死亡,因是过年他们忌讳,人没来家就签了字。这也是师父安排的,不让邪恶上门找麻烦。
之前已和殡仪馆联系好,由他们一条龙服务。小区派出所的人都知道我丈夫人走了,可就是看不见我,就与当初回来一样,谁都没有看到我。我来回上下楼梯,殡仪馆的人来往不断,就是碰不到他们。悟到平时发正念很重要,我想“不让人看见我”就没人看见我。心正念正就随心所欲,发出强大的正念就会出现神通。发正念的同时,师父也在加持我们。在殡仪馆也有一些有缘人得救。
丈夫过世时,家里的钱,现金和存折上的钱平白无故的多出很多,刚好处理我丈夫医疗费和后事,一点不多,一点不少,我没有背债,在心里感谢师父。
处理完丈夫的后事,我就和一位八十二岁的女同修到四川边远农村利用当地的习俗(农历二月十九日的观音会)讲真相。我和老同修配合劝“三退”几十人,下午快散场了,还有的人来不及劝退,我就站在稍高的地方,大声告诉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反复几遍。悟到救人的机缘错过了一次,很可能就没有下一次机会了,要珍惜每一次机会救人。
比起国内外的精進的同修,我做的还是有差距。海外的同修很辛苦,为减轻大陆同修的被迫害,做了那么多,做得太好了,也给了我勇气。
现在我仍在外地,我抓紧利用所有的时间做好三件事,不负大法弟子使命,跟上正法進程,圆满随师还。
所作,所写,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合十
- 法轮功书籍 免费下载 |
- 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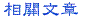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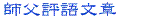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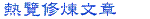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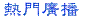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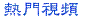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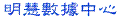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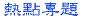
 迫害致死
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