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一念 信师信法
得法前,从小就是一个体弱多病,面黄肌瘦,少言寡语,不善于和别人交往的人,由于身体多病及家庭条件贫困,十四岁才上小学,青年时期体重不过百斤,什么活也不能干,成天以泪洗面。
得法后是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使我变成了一个身体健康,看淡名利,遇事能为别人着想的修炼人。我非常自豪的想,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我有师父,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能跟随师父正法,完成史前大愿,是我最大的荣幸。
我家住离县城不远的农村,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前,我经常参加城里炼功点每周一次的学法与交流。一次学师父经文《真修》,师父说:“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精進要旨》〈真修〉)当时同修谈各自的认识。
我回家重温这篇经文时,眼泪不知不觉就下来了,一时泪流满面,真是觉的对不起师父,师父无私的救了我,我还有私心杂念在掩盖着。我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几十年一直闷在心里,没对别人说过,修炼大法后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我还固守着这旧观念。旧观念的背后就是执着名、利、情。一是名,怕说出来不好听,对亲情有影响。二是利,做什么事情怕别人不跟我合作,远离了我。三是情,怕亲人担心,给他们造成精神压力。
放下这一执着后,我逢人就讲通过学法炼功后心身受益的感悟和变化:我有先天性心脏病无药能治愈,通过学法炼功身体上的疾病不治而愈,大法真神奇。我母亲、妻子、姐姐及亲朋好友先后走進了大法修炼。炼功点人数也多了。
迫害开始 進京讨公道
在九九年邪恶疯狂迫害法轮功时,电视、电台、报纸铺天盖地毒害民众,县“六一零”及乡派出所经常去我们村法轮功学员家骚扰、绑架、抢劫。我想这么好的功法,师父教我们修心向善做好人,锻炼身体,对谁都有好处,共产党为什么不让我们炼。我一定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大法。
二零零零年下半年我去北京打工,十二月份天冷,民工陆续回家,我就打听去天安门的路。来到天安门广场上,我打坐炼功,大约有几分钟,有两个人拽着我的胳膊就走,在后面硬拉,把我绑架到什么分局。见我什么也没回答,下午三点把我们几十位同修拉到百里外的一个看守所里关押。第二天我们堂堂正正的走出看守所。
第二天有同修约我去北京,我们冲破恶党警察的重重阻拦,正念走進天安门广场。恶警把我绑架到石景山派出所,一个恶警拳打脚踢,用电棍电了一阵说“还真经电哩”,又换了一个大号电棍,怎么也不打火,又充了一会电还是不管用。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另一个恶警用伪善的手段叫我说话,看我不说,比那个更恶毒的拿着电棍满身乱电。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底我被当地“六一零”劫持到看守所,里面关押多名同修。“六一零”叫我们写“三书”,我不写;再叫写,我就写炼功前后身心的巨大变化,师父叫我们做好人,行善事,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六一零”的人说这样写不行,不写不放人。
二零零一年四月份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劳教迫害,有的被放回家,有的回家没几天又被绑架進来。看守所监所科科长是我家属的亲戚,家属送吃穿都通过他送到我手里。有好吃的他都站在窗口看着我吃,不然就会被别人抢走,有时叫到他办公室去吃,对我也关心,我给他讲真相,他就说:“我知道法轮功好,知道好回家炼,别在这里。”我说,“这是××党对我们的迫害。”
五月一日这天,这个科长又劝我写“悔过书”,我不写,他指着关在一起的一个大学生说“他不写你替他写”,我说“你也别替我写”。由于执着于私情和面子,我听他说“我不给你写别的,能回家就行”,一看也没发现什么不好的话,就是中间留着空白,就默许了。过后我越想越不对劲,就想把那份材料要回来,已经晚了。
晚上我做了个梦,梦中有一条小溪,小溪不宽也不太深,小溪另一头连着一条大河,从西方漂来一只非常漂亮的小船,我坐在小船上往前走,越走越慢越往下沉,走到一座小屋附近,搁浅走不动了。我下船准备推着小船走,可我刚下来小船马上漂浮起来走了,我伸手去抓没抓着,就奋力去追,可小船比我快,怎么也追不上,我就顺小路直奔大河去拦截小船,到了大河边,看到小船刚汇入大河,速度更快了,我离它有好几百米远。我追到大河中心的时候,小船与我擦肩而过,我再也追不上了,就这样小船离我远远而去。
醒来后我泪流满面,那只小船不正是一只法船吗?由于我执着心太重,贪图一时的享乐,我坐的法船下沉搁浅。由于受情魔的带动,执着于私情,执着于脸面,执着吃喝,默认接受了别人写的东西。中间有空白,这空白处是不是又填写了什么,我也不知道。这空白不正是我的大漏吗?使我在修炼的路上栽了跟头。师父点悟我修炼是严肃的,不能带有任何虚假,修炼走捷径是跟不上正法進程的,所以每一关每一难都要踏踏实实的过才行。
在看守所非法监禁我四个月二十六天,又向家属敲诈三千五百元钱才放人。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下午县国保大队几个人闯到我家抢劫,把我绑架到公安局,整个晚上四个恶警轮班非法私审我,说我参与聚会。第二天上午把我监禁在百里之外的一个看守所,前两次非法审问没得到任何他们所要的东西。
第三天“六一零”叫村干部、家人来,看说不服我,就说你家的钱存在银行里,你家属不知道密码,你把密码给说一下。我说:我家的钱是孩子打工挣的,是给他们盖房结婚用的,不能随便乱花一分。再说我的密码不能告诉别人,告诉别人就不是密码了。村干部就问“六一零”怎么办,“六一零”无奈的说:钱我们不能要了,你看他那个样,收了他的钱,他出来告我们,我们没话说。
在王村劳教所反迫害
我曾经被当地六一零非法送到王村劳教所,关押在七大队。七大队和八大队主要关押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到了监号,警察马上安排两个犹大昼夜监控,寸步不离,不准给别人说话,打招呼,更不准交谈,强迫听警察和犹大轮流灌输污蔑大法的言论,逼迫放弃信仰。
几天后看我不动心,就开始加重迫害,一直面对墙壁罚站,两手下垂,不许说话,犹大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恶警更是拳脚相加。两个星期后看我仍不放弃信仰,就把我关到严管班,昼夜不停精神折磨,晚上十二点睡觉五点起床。五月份开始一天只睡一个小时的觉,持续了二十多天,晚上四点睡五点起,还没睡眠就得起床了,几个人轮班熬我们,脸对着墙壁罚站,拳打脚踢。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法都改变不了我们信师信法这颗坚定的心。
两个星期后,我和另一个同修被关在一起。由于长期被罚站,这位年轻的同修脚肿的很厉害,不能站立,生活不能自理。从零六年五月底到零七年我走出劳教所一直躺在床上,已经十个多月了,劳教所也不放人。
后来我想,不能再接受他们的无理迫害,恶警及犹大背后是受旧势力及邪恶的灵体所控制而对我们法轮功学员加重迫害的,我们不能接受也不能认可,法轮功学员要堂堂正正,不管在任何环境下都要讲真相,坚持正信,我不接受他们的任何无理迫害,我也不怕他们对我的任何迫害。从绑架那天起我就没有怕心,我要给他们讲真相,同时清除解体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
有一天,犹大写月小结,叫我对墙面壁思过,我说我没什么错思什么过呀。我不配合他,他就动手强制我,我大声和他讲理,制止他这种邪恶的行为,告诉他这样做是违法的。这时邪党大队长和教导员来了,我继续和他讲理,他们看着我笑了笑就走了。这时犹大的邪气也消了,不敢再那么邪恶了,我睡觉的时间也提前了,从凌晨四点、五点改为十二点。
在严管班里恶警对法轮功学员不但在肉体上折磨,每天除睡觉、去厕所和洗刷外,都得在小板凳上坐十七—十八个小时,头和胸都要挺起来,双膝靠拢,两手放在膝盖上。否则就要挨打受骂,达不到标准就加点加重迫害。出门去洗手间都得大声打报告,声音小点,都得拉过来重打,再不行还得重来。去洗手间中午去一次,下午去一次,规定大便三分钟,小便一分钟。
有一天又放录像,我们在后排坐的三个人都到里屋去坐,别人一看我们走了,他们也都走了,值班的大班长就找来了警察,问谁先走的,值班的说是我把他们带走的,警察说:算啦,都不愿意看就别放啦。
我想他们怎样对我都无所谓,我也无怨无恨。我就要正一切不正的,决不听邪恶的安排。有一天早晨,值班的天不明就叫我到外面去坐,并且张口就骂。我说你值班也不能随便骂人,你骂我就不出去。他就强行往外拉,把我的上衣都拽烂了,也没有拉出去。我大声和他讲理,警察去了看了看也没说什么就走了。我问他为什么骂我?为什么把我的衣服拽烂?后来他觉得自己不对,就拿了自己的一件好褂子赔我。我说:我不要你的衣服,我就是不让你迫害我。
八月份警察又对我们强制转化。我想所谓的做转化工作的人,有的是跟大法结了缘的,由于承受不了压力,做了背离大法的事。通过我们多次交流、切磋,他们归正了自己,有的还写了声明,只有个别怕心重的不敢说话、不表态。
有一次一个刚被绑架来的同修走入误区,被警察利用来做我的转化工作。我严肃的告诉他,你自己走的路对不对你都不知道,还说帮助别人。他没有吱声,三天后这位同修醒悟了,写了严正声明。
九月份的一天,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交流,恶警李公明从外面窗户往里看我们,问我有没有认识,他们回答没认识,李公明说没认识明天参加劳动去算啦,别做工作啦。我说我不参加奴役劳动。他一听大为恼怒,走过来对我拳打脚踢,向我胸部猛击,又左右两个耳光,恶言恶语的说,不转化,不劳动,要加倍整你。
十月十五日,两个包夹值班的恶人向我脸上吐烟圈,还恶言恶语骂我,我善意规劝一直不听,我说法轮大法不允许你们迫害我。恶警王新江和宋南叫来了四五个打手,把我抬起来,我不停的喊“真、善、忍大法”,“不准你们迫害我”。他们把我抬到会议室,按倒在地上,有一个大个子二十多岁叫田龙长的人,两手捂住我的嘴用手指猛捏,当时我的牙齿被他捏掉一颗,捏歪倒四颗,满嘴流血,有的猛压我的大腿,有的用力压在我身上,有的在我头上身上拳打脚踢,几十分钟后才放开,当时恶警王新江、宋南在一旁监督。
由于牙齿被捏的歪倒,不能吃饭,十天后他们要给我灌食,遭到拒绝后,就强迫抬我去卫生所,按在椅子上,两只手背铐着,两只脚别在椅子里,两边各有一个人用脚蹬住,后边一个姓王的包夹恶人脚踩住手铐用力一蹬,我疼的大叫,我说你们再迫害我就告你们,我不能被灌食,我的牙被你们打动啦。负责灌食的卫生所长看我的牙,我不张嘴,后边的人拽头发,两边的人捏我的嘴,灌食的看到了,不敢强行从嘴下胃管强灌了,就拽头发捏嘴从嘴里灌。从那以后直到走出劳教所的半年时间里我只能早晨喝一勺玉米面汤(五分),中午吃一勺菜(五角),晚上一勺菜一勺面汤,每天生活费一元一角。
零六年除夕晚上点名,由于抗议恶警对法轮功学员长时间的残酷迫害和怂恿恶人干扰迫害,点到我的名字时我没有应声,恶警李公明大为恼火,拿着硬纸板做的点名册的尖角在我脸上不停的四处乱磕乱砸,还恶言恶语的乱骂,什么难听骂什么,从没听过的恶语都从他嘴里出来了。
零七年王新江被邪党重用当副大队长后,把我们硬调到一间小房,一天到晚不见太阳,白天还得睡几个值班的,晚上十几个人睡在里面,气味非常大。白天我们坐在不到一米宽的过道里,要我们都回头朝里坐,我就是不朝里坐,我朝外面坐,在门口,看到王新江我就要求他给我们调离地方。有时出门在走廊里给他讲,王新江很少在严管班停留,以后我看到不管是警察大队长、教导员,还是所里的什么人,还是省里的什么人,我都要跟他们讲道理,说明事实真相,要求调换地方。后来允许我去晒太阳,也允许我到以前的床上去睡,我说光叫我自己晒太阳还不行,他们也得需要去晒太阳,我们都得搬过去才行。
有一次在会议室里,警察队长半开玩笑的说:哟,你现在高级了,队长的高凳子你也敢坐。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对社会、对人民都有好处,我什么时候也不低级。
有一天恶人又在打骂我,我正面制止他,警察就叫我去另一号室,里面有一个刚被绑架来的同修,用两个大型铐子打着背铐,铐在椅子上,下着胃管,一头用胶带粘在头上。这位同修已经在当地看守所绝食十三天,又绑架到劳教所。两个犹大在屋里干着活,监视着这位同修。这时同修说要小便,两个犹大漫不经心的说队长不在这里我们也不当家啊,还在那里干他们的活。这时这位同修又大声的说要小便,把头用力一甩,把下的胃管甩出来啦。我说你们不当家,可以去找队长,队长叫不叫去,没你们的责任,不一会犹大去找警察好久才回来。
恶警王新江来了,看了看那位同修,又看了看我,气急败坏的说,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是队长叫我在这里的。他赶我回去,我不回去,看他们在干什么。他抓着我就往外拉。别看他一身肉,就是拉不动我,他又叫了两个包夹往外拉,到了铁门口时,我抓住铁门就是不动,王新江恶狠狠的用拳头猛砸我抓铁门的手,又用脚猛往门里跺,拽到五号监室,按倒在地上,拳打脚踢,还往脸上掴耳光,打的鼻子、嘴都出血了,满脸都是血,身上也是血,躺在那里好长时间没能起来,王新江叫来犹大大班长,让他用湿毛巾把我脸上的血和衣服上的血擦了,叫他看着我,迷迷糊糊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是如何迫害的那位同修,到吃晚饭的时候把我抬回到严管班。
一连几天我不吃不喝,警察大队长去找我,说你有什么事尽管说,该说的就说,该吃的也得吃。我说有事找队长算不上什么错吧,你想那位学员不吃饭你们强给他灌食,灌到肚子里不让他大小便那能行吗?我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信仰是我们的自由,你们不能那样铐着迫害他,我说的也不算多,王新江就那样打我骂我迫害我,我也不怕他打,我也不怕他骂,我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警察大队长只好说,他这样做是他的不对,叫他给你赔礼道歉。第二天王新江来了,他说,前几天是我的不对,我不该打你骂你,以后保证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我说,我也没有什么怨,也没有什么恨,你这样打人骂人是对你自己不好,再说你们当警察的也不能随便打骂人吧?!
绝食七天后,他们又采取了另一种迫害方式。知道我不同意灌食,就把我绑架到三五八医院强行查体,陪人往车上抱我时说我体重不超过三十公斤,检查结果一切正常。把我的一只手铐在床头上,另一只手叫陪人按着,一瓶一瓶的打了一天吊瓶,都是不明药物。我说坚决不打了,医生说你不吃就得打,你不打把脚手都铐上也得打,你吃就不打了。到晚上我想,我虽说几个月没吃主食了,七天不吃不喝也好,十天不吃不喝也好,一点也不感觉饿,精力非常充沛,身体气力也很好,虽然一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从没感觉困过。劳教所里很少有机会洗澡,偶尔允许洗一次,一年四季都是洗凉水澡,每次叫洗时我都洗,就是三九严寒从不间断。我一个好的身体,不能被他们残酷的迫害,他们虽然说打的是营养药,实际上这种药对我的身体破坏力极大。到了第三天,感觉四肢无力,筋疲力尽,肉象刀割一样的疼。我想我得早点离开这鬼地方,不能再让他们迫害我。我说我就是不在这里,在这里我坚决不吃,爱怎么样怎么样,下午就把我拉回劳教所。恶警说你回到劳教所里不稳定。
有一次我见到警察教导员就问他,不准克扣、挪用在所人员财物,为什么扣我的现金,李公明说你签字了吗?我说管财务的要扣我的伙食费和医药费,我没什么病,你们强行给我打针,药费我不接受,我也不签字。他说没签字不算数,也不起作用。你在这里什么也不写,一年给你加一个月的期。我说我没期,我也不接受加期。
有一天恶警李公明要赶我回严管班,我说我不走,前几天你说好的叫我在这里就行,今天为什么赶我走,你想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不行。到了下午,李公明叫来了几个打手把我抬到严管班,放在床上,我说我就不在这里,我也没什么怕心,我就不接受你的迫害。我起身想走,刚下床一头栽在地上,待了段时间,有人问李公明怎么办,他说再把他架到会议室里去吧,就这样又把我抬回来啦。
有一天警察大队长说你快走了,一个月给你加一天,加十二天。我说我从没想过这事,我没犯法,也没犯罪,我一天也不该待在这里。是当地六一零加的罪名。二零零零年去北京上访,非法监禁我四、五个月退还,勒索钱财几千元,几年了也不还,还变本加厉的迫害好人,天理不容。
在恶警绑架我第一年多时,恶警看我不吃饭,又一次把我拖到医院迫害。第二天上午王新江和管账的警察匆匆忙忙到医院叫医生拔了吊瓶,叫陪人把带来的东西全部带走。我刚走出门王新江非要给我戴铐子,我说我都被你们迫害成这样啦,还给我戴铐子,我不戴。就这样他们又把我拖到劳教所。
家里人多次去看我,好几次都不让见面,后来听出来的同修说了我的情况,家里人急了,去找当地六一零,他们怕担责任,给开了信才让见了次面。我给家里人说:这里的事你们就别管了,是当地六一零把我送这里的,什么事都有他们负责。我回家的那天,六一零推卸责任不去接,叫管区压大队去接,最后还是家属接的。
回家后我的身体恢复的很快。每一步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过来的。感谢师父,感谢大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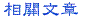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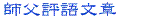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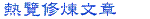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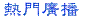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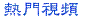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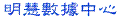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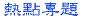
 迫害致死
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