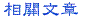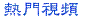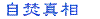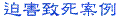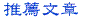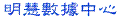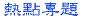甘肃天水法轮功学员尹小兰遭迫害经历
我是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佛法的。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江泽民为首的政治流氓集团及其帮凶先是颠倒善恶,污蔑教人向善的法轮大法,并制造“天安门自焚”事件和各种污蔑大法和师尊的谎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群体残酷迫害,非法抓捕、审判、关押、运用各种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
面对迫害,我去国家信访办上访,遭到了几十个便衣警察的毒打与谩骂,被天水公安局接回,关押在天水市看守所十五天,并强行勒索二百五十元现金,释放后被单位非法开除公职,直接参与迫害我的责任人是天水地区燃料公司经理白保安。
为了让世人知道法轮功弟子被迫害的真相,为了让世人知道江泽民及其帮凶制造“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真相和各种污蔑大法和师尊的谎言,我们省吃俭用、用自己的工资制作真相资料,揭露邪恶的谎言,揭露邪党对我们修炼人的残酷迫害。邪党怕它们的谎言和恶迹被世人所知、先后绑架了我和唐琼、王有明、赵兰州等几位做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中旬一天,我正在街上行走,一辆轿车突然停在我身边,下来七、八个壮汉把我围住连拉带扯的往小车里推,我竭尽全力不进他们的车,并大喊:“土匪绑架人啦!”他们用拳头打我的脸,我的鼻子、嘴里流着一股一股的血,参与暴力绑架我的这些人是天水市秦州区公安分局联合行动组便衣:刘亚顺、张鹏举、张文彬、刘增强、杨晓峰等。
我被他们拉到一个宾馆的客房里,一女警将我全身搜遍,所有东西全部拿走,口袋里近八百元现金一分不留全部拿去,所有被拿走的东西,一概没有任何收据,整个过程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个人身份证明。然后将我劫持到秦州区政法大楼政保股关押,我被铐上双手坐了三天三夜(当时政保股长是裴桂林)。
然后他们将我移交到麦积区公安分局,关进一个带大铁门的两层小院里,期间恶警冯继堂、武红霞、刘萍的轮番对我酷刑逼供,冯继堂、武红霞用一寸多粗的木棍打我,棍打断了再换一根,打完了再问,问完了再打,并强行令我站在墙角,由恶警冯继堂打耳光,不知打了多少下,只觉得脸麻麻的、头又大又胀,一股热乎乎的血顺着衣服往下流,而且不让睡觉,不让闭眼。这场严刑逼供持续了十二天。
恶警将我秘密劫持到秦安看守所关押。当时我被打的遍体鳞伤,一条腿不能行走,头脸肿的像充气皮球,眼睛肿成一条线,数九寒天除身上穿的一套衣服外,没有任何生活用品和衣物。
五个月后,天水市公安局来了两警察非法提审我,我问他们我犯了什么罪被秘密关押秦安,为什么不通知我的家人,而且不给任何生活用品。他们不回答。
我被绑架的一个星期后,天水市秦州区公安分局联合行动组的裴桂林带一警察闯到我儿子所在学校天水市一中,通过校方,将正上高一、未修炼的儿子绑架到天水市戒烟所,并用手铐铐住双手审问,后将我儿子双手背铐面对墙站立两天两夜。第二天早晨九点,裴桂林等又将我丈夫从家中绑架到天水市戒烟所,十几个警察围住他非法审问,并没收他身上的两部手机。
丈夫被抓时,他的父亲正病危,家中只有一位八十岁老母和一个卧床不起的妹妹,本地没有亲戚,急的老母哭天喊地的拜托人找儿子,而这一切公安局那些警察全知道并亲眼目睹,可他们不顾老人死活,毫无人性地强行将我丈夫非法关押十四小时,晚上十一点多才放回去。丈夫回家的第二天早晨十点多,我的公公就去世了,老人去世前一个小时我儿子才被放回。由于恶警没收了我丈夫的两部手机,给他办老人后事带来极大的困难。
二零零二年,我被非法关押在秦安期间,被医院诊断出胆结石,需马上手术治疗,否则有生命危险,我被保释回家,住院治疗过程,未进行手术,又被天水市秦城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关押到天水市看守所。
天水看守所非法关押着很多法轮功学员,狱警强迫我们进行奴工劳动、背监狱规则、每周做自我检查、照犯人相、早晚报数、听管教训话、强行按各种手印,还要给管教洗衣服,并且随时和定期大安检大搜身,如有不从和争辩,必遭毒打。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八日,天水市秦州区法院非法开庭审判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我和王有明被非法重判十一年,唐琼被非法判重判十二年。开庭前我家人未收到任何法院通知。我们上诉,法院不作任何答复。遭恶警酷刑折磨、胳膊被打断的兰州法轮功学员张金梅被秦城区法院非法重判十九年。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日,我、唐琼、张金梅、王有明和另两位男性法轮功学员被分别劫持到甘肃监狱女监和男监迫害。
在甘肃女监队,恶警将我们全身扒光非法强行搜身,所有物品都被拆烂和撕开,80%的物品被没收。搜到唐琼时发现了师父的经文,恶警队长华某抬手就是几耳光,张金梅因阻止恶警打人,被铐在大厅地面一条长铁板上,人只能蹲在地上,不分昼夜铐了一个星期。
我们在监狱受到非人的折磨,每人都被三名“包夹”日夜监控,每天恶警轮番训话,强迫奴役劳动、报数、穿囚服、背监规、写思想汇报、逼看污蔑师尊和大法的电视录像和书、逼看央视造假新闻,法轮功学员之间不能接触、不能说话、不能学法炼功、不能讲法轮大法真相和揭露恶警对我们的迫害。隔几天将我们和犯人一起弄大厅里扒光衣服搜身,大厅在一楼几个大窗口敞着,外面时不时有人走动,就在这光天化日下,她们非法强迫我们脱光衣服由她们随意搜身,我们的物品随时被倒出来检查,稍有不从和她们认为的危禁品,不是被打就是上刑具关禁闭,此类行为构成了严重的侮辱罪。
一个月后我们分到不同监区遭受非法迫害,我被分到一监区(这里已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在这里我们受到超时奴役劳动、强行转变我们的思想、每天强行到办公室听干警无理的训话1_2小时,“包夹”不分昼夜的跟踪监视,强行背监规考监规,报数、写各种歌颂邪党的稿件,强迫看污蔑师尊和大法的电视录像书刊,强迫看中央造假新闻,不许我们学法炼功讲真相、不许我们同修之间来往说话。
我们没有休息日,每天早晨七点出工,晚上十点收工,中间只有两次吃饭的时间,就我几十分钟的吃饭时间也被她们用来为她们自己赚钱,刚吃完马上被要求剥大豆、剥蒜、糊纸袋、并要求定质定量,晚上收工回来接着干,直到半夜十二点多才收工,完不成定量接着干,质量不合格就反工,啥时干完啥时睡觉,第二天早上七点正常出工,生病不能休息必须出工,犯人接见家人时间可长达一小时至二小时,法轮功学员接见家人只有二十分钟,有时只有十分钟,接见时被狱警监听,并作记录,有时外边家人身边坐一名干警,我身边坐一名干警监听,犯人能吃接见餐,法轮功学员不能吃,不让我们自己买生活用品,不让我们自己打热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犯人可随意上下楼,上别的号室,法轮功学员不能,犯人可随意接触任何人,法轮功学员不能和别人说话,任何一个犯人都可以监视法轮功学员,汇报其行踪,并有奖分,监视法轮功学员的犯人每月都有奖分,一次过年前我丈夫和儿子来看我,儿子想妈妈,可接见室的干警和监区干警不让他们见我,无论他们怎么说好话都不让见,无奈他们含泪坐火车返回天水,女子监狱对待法轮功学员从不讲法律,是非常邪恶的。
法轮功学员苏金梅因看师尊经文被监区恶警大字形吊在间道卷闸门上,两脚尖踮地整整吊了三天三夜,放下后又将双手铐在水房暖气片上几天几夜,不让任何人给她送衣物食品(夜间非常冷),有专人看管,她因不放弃大法修炼被关禁闭室遭男性恶警毒打。
二零零三年后半年,一监区又送来一位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一个星期后被迫害跳楼身亡,而女监段监狱长在千人大会上却说她畏罪自杀,逃避改造,咎由自取。
二零零五年底,我因胆结石动手术,手术后回女狱内院休息,规定手术后休息二十天,而监狱只容许我休息一个星期(就这一个星期也只能坐着不能躺着),接着就被强行送入监队强行“转化”,对他们这种非法迫害,我找遍这里所有干警,要求回内院休息养病,她们不予理睬,强迫我写“转化”书。
那一段时间监狱所有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全部非法强行隔离“转化”,一监区受迫害的同修杨秀琴、王爱兰、丁桂香、马玉琳她们都被单独隔离,每人有几名恶警承包迫害,昼夜有三名犯人看守强行逼写“四书”不让睡觉、不让闭眼、困的睁不开眼就用火柴棍将眼皮支起来,每天只能吃馒头喝开水,直到“转化”为止。
非法逼迫我们在全监区犯人会上逐个发言表示自愿“转化”并录像,不从者当场由监狱警务处五六个男性警察实施酷刑“转化”。
在这地狱般的魔窟里是没有法制的界线,恶警完全任由她们自己的利益、情绪、兴趣决定一切,视法律为儿戏、知法犯法、任何一个关押的人触犯了她们的规定,或者没有按照她们个人的要求做,她们不但惩罚当事人而且还要惩罚全体犯人,我们也不例外、她们明知发生的任何事都与我们修炼人无关,可她们每次都将我们和犯人一同惩罚,如全体罚站,让太阳曝晒、一遍一遍唱歌、一遍一遍的背监规,罚坐(最长一次从下午6点坐到半夜12点)、全体写检查、一遍一遍开会强制发言,有时长达一天一夜的关闭厕所,不让上厕所,围着操场跑圈跑不动也得跑,一遍一遍走队列到她们满意为止、饭菜少时饿着,多时撑死也得吃下去,不能剩、不能倒、不让带进号室只能吃下去。下工后饭菜放着不让吃,要唱歌,唱不好接着唱,唱到她们满意为止(下工后又累又饿根本没精神唱歌),强迫所有人每月写她们规定的各种稿件他们的恶行罄竹难书。
在此我呼吁全世界爱好自由民主的善良的人们,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善良的人们关注还继续在甘肃女子监狱遭受非人生活的法轮功学员。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html/articles/2011/5/29/125623.html)
- 法轮功书籍 免费下载 |
- 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