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二岁老人的得法故事
童年
我童年时生活在一个贫寒的家庭。十三岁那年的春季,身染重病半年多。一天晚上,我跟妈妈要饺子吃,我妈说重病想吃饺子不是吉兆,当我妈把饺子端上来,我只吃了一口,感觉是马粪味,放下就睡过去了。
梦中的境界至今记忆犹新:两个人把我从家里领出来,一路上尽是山水花草,最后来到一座城市,人来人往不知是干什么的。后来进了一个宫殿,里面的人我都不认识。坐着正面的一个人问我:“你是在这等着还是回家呀?”当时我并不知让我在这等什么,我就想到:如果时间长了我母亲找不着我,会着急的。所以我说要回家,只见那人吩咐领我的两个人,“还把他送回去。”就这样把我送回来了,我只记得到了家门口摔了个跟头就醒了。我妈说我已经睡三天三夜了。
信神的起源
回忆自己这一生的思想观念的形成,离不开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只举几例。
(一)我的童年与众不同,别人都是小朋友们在一起打闹玩笑,可我总和老年人呆在一起,比如我有个五叔,是个看相书的人。我受他的影响,形成了听天由命的思想,并在我脑子里生根发芽了,所以历来对无神论的宣传是不闻不问,好人说我“魔症”,坏人说我“迷信头子”。
(二)我在童年最喜欢追求真理,作为坚定自己的信心。在日本侵华时期,我地区出现一个借尸还阳的女人,此人是我亲姨娘的亲戚家姑娘,在她还阳路过枉死狱桥上,碰上我亲二姐(因我二姐是服毒死的),我姐拜托她给母亲带信,给我妈要钱花,我得知后每年节风雨不误,给我二姐上坟化纸。
(三)童年见过我地区某地有一个特大的坟墓远近闻名,是因为有一户人家,主人对财产支配有道,而且不太计较得失,惜贫心比较大。他舅父是贫苦人,就来求借,时间长了,欠的钱多了,至死也没还上。这家主人有一天夜间做了一个梦,看见他舅父来还账,早晨醒来一看马栅里生下来一只小骡子。他想这可能是我舅父转生。这个骡子在他家一生做出了几件惊人的大事。只举一例:有一次夜间他家来了一伙三十多人的马队贼,他们把一个老头放在锅里用水煮,问他银子窖在哪里,不说就折磨死。其实这位老人不是当家主人,根本不知道银子在哪,此时这个骡子挣断嚼子,一直跑到集镇门口大叫,主人出来一看,知道一定是家里有事,急忙带上手枪骑骡子往回跑。骡子一直跑到山顶才站住,主人向村中一看,知道是家有贼了。于是对着自家方向开枪,吓得一群贼上马飞跑回山去了。主人回到家里,他叔叔在锅里坐着,下半身的肉已经煮熟了。
这骡子作出救主人的事不知有几次。骡子老故死后,主人不忍,只当是他舅父所以修了大坟墓。这坟始终有人在节日上坟化纸,是恶党来了才给铲平了。象这类真实的故事,在我长大直到成年时代一直在探讨。在这方面直接的和间接的,可以说我知道可不在少数。在十八岁那年,正处于邪党搞公社化,我产生了厌世思想。当年腊月初八,去登高山出家。我步行好不容易登山到寺院,那和尚一句话把我说的心寒。他说:“任何人想出家,没有公安局的批条不收徒。”从此对邪党背上了不可解的包袱。
“文革”中坐牢十年
“文革”时期,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坐牢十年。
自从我出家的名声一张扬出去,引来一个信仰道教的人劝我入道,那年我不满二十岁。当时我走投无路,一心想修炼。听说韩湘子也是这门中的先徒,所以在这一门中认真修炼。没过几年,邪党发动文革,把道教划为反党的邪教,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我们一起修道的四人被判刑入牢,从那时起就体会到邪党的政策残酷至极。
入监后,不准家人见面送食物,把监狱生活口粮一断,这叫绝招。一天每人半斤玉米糠,早上一两晚上一两中午三两,谁有不符合监规处,每人一天一两。再强壮身体的人,入监一月就变成医院那个活针灸图,脱衣服谁也不忍心看一眼,三天两头往外抬死人。凡属于年老体弱带病的人,入狱后没有能活着出去的,只有年轻体壮无病的人,才有可能忍耐到底活着回家。
在县看守所这一鬼门关过去后,又到了劳改队。虽然生活能充饥,但是强迫劳动还是肉体的残害,还要强制学习。三年的看守所、七年的劳改队,这十年刑期度日如年,自己也不知是怎么活过来的。
在劳改队的肉体虐待。我三十七岁那年,我从高空台上掉下来,把右胯骨摔伤了,生活不能自理,连身都翻不了。受罪至第六天上,邪党的狱警才给找一个犯人中会骨科的给我调整。过去一个月了,生活能处理了,就强迫我出工劳动。那段时间,劳动很吃力,甚至疼痛难忍。有一天我想,还有七年徒刑,这罪怎么遭,不如投水自尽解脱此地。我正要投水,被同伴发现。群犯里也有见证我实在难以忍受的情况,跟上头说了,这才给假让我休息几天,缓一缓。
劳改队所谓的改造政策,极力强制学习。所谓的思想改造,结合劳动改造,让你变成所谓的新生。当时我听他们讲的骗人鬼话,越听越生气。但不好好学习就被批斗。他们的批斗分明鬼叫狼嚎,你不接受就得体罚肉刑。在这阴暗的日子里,时间又长,怎么办呢?为了摆脱,我就参加学习,我内心目的是为了习练文字,将来可能有用,总比荒废了好。开始学习报纸,后来给我几本哲学上的,让我学。看的还不少,从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杜林、费尔巴哈、达尔文等等,我如七年苦读书一样,不但没中毒,倒让我知道无神论在地球上是一棵大毒草。
得遇大法
一九八零年,我刑满回家。我童年时就是邪党对立面人物。生活在这个时代,因我思想与众不同,邪党把我害的家破人亡、一贫如洗、无依无靠。我一人生活,坏人用恶言攻击我,老实人见我不作声,他们是怕邪党把他们当成我的同盟。因此我有任何难关也没人上前帮一把。无奈,我到外村找一个人家嫁了,过着艰难的日子,没法维持。在无路可走的阶段,低下头来认了一个义父。义父年轻时在中央报社当记者,老了才回家。义父把我们全家四口人带进了北京城,给一家木器公司打工十年。回老家盖房,重建家园。因钱不够用,又返回北京城。在打工后期,正是法轮功开始受打击。有一同修花钱买几本大法书送给我,教我功,完全是义务,一分钱没收。他说:你太贫寒,同修帮你得法修炼,是咱师尊让弟子这样做的。我受到感动,认定这是正法门。在二零零零年正月开始,学会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有一次同修教我发正念,学完后就再没见着他。至我回家的四年中也没找到一个同修。回家后,只有门中盟兄是同修,得法已八年了,经常给我帮助。师父慈悲救度、同修无私帮助,我的修炼也在提高。通过学法,知道如果因为怕邪党迫害而放弃大法是下地狱,坚定跟师父修大法才是正途。几年来一直认真学法,看周刊,逐渐升华。
体验大法的神奇
我在大法中修炼,亲身体验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神奇,不知多少次了。
二零零二年春季的一天,我高烧不退,烧的心里摆茫(方言,心里发慌的意思)。身上热的烫手,我去医院检查,结果医生量体温相当正常,医生说没有什么病症。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消业,不是常人的病。
二零零六年秋天,发现一桶花生油已经变成黑色的花黄水样了,吃一点嗓子都冒烟。扔掉它又觉得可惜。我心生一念,炼功人能使毒药变甘露。就这一念可好,这桶油吃到完根本没有坏味。从此我深感大法给修炼人展现的神奇。
二零零七年秋前,有一次我突然腰疼的不能动。第三天的上午十点多钟,有一同修来我家,告诉我:“你那不是腰疼,是黑手乱鬼在迫害,赶紧发正念。”我就立即开始发正念,一连发了两个小时后,我的腰真的不疼了,活动起来完全恢复正常。我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二零零八年正月,因我家的卫星接收器有了干扰,第一次我认为电视机有故障去找修理,可他说没有毛病。我又找同修帮我发正念,结果把干扰排出去了。不久第二次又来了干扰,修理工还是说没毛病。又找两个同修帮我发正念,结果没排动它,最后我实在没有办法,我给师父上香求师父给排除干扰。我礼拜后起身打开机子,完全恢复正常。这让我满心的感动,心生一念:无论以后在什么样的处境,我就是坚修到底。
向内找到自己的不足
虽然有了坚定修大法的信心,但是还存在很多没修去的执著心,可以写出来,向师父向同修汇报实情。求安逸心,饮食习惯于讲究营养,追求长寿健康,怕受迫害,这些直接阻挡我大量证实法、救度众生。只是对至近亲友才去救去讲真相,人多了就逃避。只有炼功、发正念,基本上能做到位。学法也是在家学,没有小组提高也慢。
矛盾中提高心性
近几年,本村有两个人让我教功。我耐心的教他们五套功法,我非常用心的慈悲对待同修,所以处的比较深。二年后他们都放弃了修炼,回到常人里,我感到痛心,后来又给我在经济上受到损失不小,更使我痛心,因此对讲真相有些灰心,觉的世上的人心正的太少,不通过知己就愿教功了。有一天学到《洪吟》〈谁敢舍去常人心〉:“常人只想做神仙 玄妙后面有心酸 修心断欲去执著 迷在难中恨青天”,使我悟到那两个昔日同修的事是在去我的利益之心,修心过程中感觉心酸正是在魔炼我还放不下的心,从此再也不因他俩痛心了,这一关才过去了。
对正法修炼的体悟
我在修大法中学习《转法轮》、新经文与周刊,我悟到修炼人只有在修心断欲去执著上下功夫才能从各方面达到同化大法,人的一切观念都是旧宇宙法形成的,从微观到宏观都得从量变达质变才能彻底同化大法。在大法中修心性,修自己的一思一念。修的过程中去掉一个执著心就能升华生出一个正念,通过魔难考验去人的执著返出人的真性,最后把执著心断绝达到一尘不染,达到完全同化新宇宙,也就是走出世间法。
师父在《转法轮》里告诉我们“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绝对的真理。如果修心功夫上不去,五套功再多炼也是枉徒劳。我体会到人的执著心,通过吃苦才能去掉,若是说一说、写一写、表表态就能去掉执著心,那简直是水中捞月,纯属笑话。
只有在沐浴大法中,随着正念的升华,去掉后天思想观念,才是由神念代替了人念。正法时期修炼所遇到的魔难,就是修炼过程中在法中升华、同化新宇宙的过程。大法弟子只有正念正行才能闯关。
我小学三年文化,没有能力把修炼的升华表达完善。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html/articles/2010/4/1/115814.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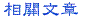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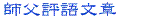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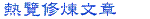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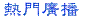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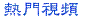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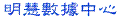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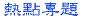
 迫害致死
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