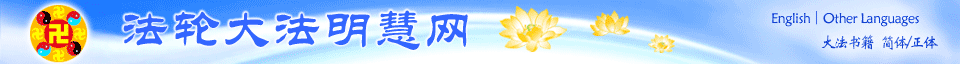【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進京护法、正念闯出魔窟
我是广州第三期师父面授班得法的弟子,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党开始镇压大法、铺天盖地的就象天塌了一样,毁谤、诬陷、谎言充斥着每一个角落。从那时开始我就走上一条维护大法的路,四次進京护法,三次被拘留、一年非法劳教、一年多关洗脑班。
二零零零年五月,我和四个同修在北京天安门庄严的打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警察、便衣、武警疯狂的扑过来抢横幅。我们不让他们抢、紧紧抱着横幅,其中一同修被武警用对讲机打的满鼻子都是血,在拉我们上车时,我与警察论理又被打倒在车上。
被抓到北京前门派出所时,我们都不报名、后来一个警察怀疑我不是中国人,可能是新加坡人,就把我带到地下室,每一层的铁笼里都关了很多同修。那个警察把我带到一间房间把手铐往桌上一放,告诉我不能来北京打横幅。我回答说:“我来是告诉政府大法好、真善忍好、停止迫害。所以我一定要来的。”接着警察叫我背两首《洪吟》,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不会背,这时才知道平时学法少,忙于辅导站的工作而没有踏踏实实的学法,惭愧啊!那怎么办?就背第一首《做人》吧,冲口一出我竟然全背下来,很神奇。警察又把我带上一楼。这时一起来的同修都被绑着在地上和反背铐着,我就过去帮他们松开。晚上,警察把我带到办公室,有个处长跟我讲:“你订了饭店没有?”我说:“没有。”他又说:“美国有美国的法律,中国有中国的法律,你来旅游、观光我们欢迎你,但不能在天安门打横幅,这不是法律,是天安门的规定。我告诉他们我是来表达心愿来的,警察就要我走,我不走,我坚持要和同修一齐走,最后警察就把我堵在大门外。第二天,见到了从派出所出来的同修,他见我没挨打就说我白来了,当时我想是不是再去挨一次打才算证实了法呢?真有点迷茫了。后来看到师父讲法才知道走出来是为了证实法,被关被打不是目地,可见自己的一念是多么的重要,符合法,还是符合旧势力,这个同修后来被迫害得很严重。
二零零一年年元旦,我和同修又一次来到北京,当时北京非常邪恶,资料点破坏的很厉害,协调人就安排我们租房建资料点,我们两个人包括北京发资料的同修都不会电脑,怎么办呢?协调人就让我们先把电脑搬回来,然后去买了四台打印机和各种耗材,一切准备好了的时候,有一个会电脑的同修与我们联系上,这样资料点就开始运作了,我们把赵昕被迫害死的真相用彩色照片打出来给同修发。把真相资料装在信封,贺卡让同修往外省发。资料点的同修生活是很艰苦的,每天吃两顿,早上咸菜白面条,下午青菜、咸菜米饭,很少吃肉。那年冬天,北京都下雪,北方和南方不一样,南方很热闹,北京冬天的大街,楼内都是静悄悄的,就是棉被把打印机垫着,声音仍象机器一样轰轰的响。就这样做了一个月。过年后,我们交流后觉得,应该回当地做好整体讲真相的协调工作。
回到南方,原来到处在通缉我,这样就有家回不去,被迫流离失所,后来被邪恶手机监听而被绑架。在看守所被关押两个月后,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看着昔日的同修邪悟了,真是很痛心。那里的恶警对“转化”的学员就很伪善,不用干活,有书看,有球打,有电视看。坚定的学员就逼着每天干十五个小时的活,不让接见,带红牌严管,不许大法弟子互相说话。我觉得不应该承认这样邪恶的迫害,大家就反迫害不干活,罢工,所里非常紧张,整个专管大队的工厂那天都是静悄悄的,把一切剪刀等工具全部收走,同修们都看着我,我微微对着他们笑,给他们鼓励,由于我的稳定,普犯们很多人向我竖起大拇指,中午狱警就把我带出去,所长、管理科长、教育科长还有专管大队指导员,对我進行围攻,我据理力争,不让钻空子,最后没办法就把我调到三大队。
中共的劳教所是名符其实的血汗榨汁机,每天做十五个小时的手工活,做各种玩具、发夹、珠链、假花。每天吃的发霉的米,没油水青菜、瓜类,连肉都没有还扣一百二十元的伙食费。上午九点,下午二点干累时就出去集体跑步,跑精神了就回去干活,那里的狱警都打人,干活慢就被拉出去挨打,用狱警自己的话说他也没办法,普犯赚不到钱他们就没奖金,挨批评。我坚决不配合,但是每个同修状态不同,在软硬兼施,又拖又拉的过程中同修们都配合跑步了,我每次站在树下不去排队,最后对我没办法,就说我高血压,不能跑,可是我从来都没有高血压。
到释放我的时候又以顽固不“转化”为由,加了我一个月的刑期。释放那天,为了制造恐怖气氛,吓唬坚定的同修,在操场上脱光我的衣服搜身,戴上手铐出所,来到所部,单位与“六一零”公安在那等着我,又一次把我直接送到洗脑班。那个洗脑班办在收容所,管理与劳教所没什么两样,还每个大法弟子配两个夹控。
二零零二年师父生日那一天,我们集体开始绝食要求无条件放人。第二次绝食躺在医院时,夜半了,我觉得生命走到尽头了,也许见不到自己孩子了,心里一阵难过,这孩子几年来因爸爸妈妈被绑架时吃了不少苦,虽然舍不得,但他也是师父的小弟子呀,众多的家庭都也在危难中啊,不就一死吗?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意识越来越迷糊,忽然,整个身体变成了一盆沙子向外飘散,最后仅剩一点意识,我觉得可能要死了。这时脑袋里显出师父的法:“我能最大限度的放弃我所有的一切,所以我能解开这一切。”(《瑞士法会讲法》)接着“我炼功是这样修炼过来的,我带有这个东西。大家坐在这里都感到很和谐,人的思想中没有邪念,连吸烟都想不起来。将来你也按照我们大法的要求去做,你将来修炼出来的功也是这样的。”(《转法轮》)我的意识一下清醒了,我是师父的弟子,大法更新的生命,师父能解开,我也能解开。飘散的粒子就不断的飘回我的身体内,当聚合上的时候我完全清醒了,时间是深夜的两点半了,前额的地方出现一首《洪吟》〈访故里〉,读完后我的眼泪象断线一样流不止。第二天单位领导来看我,之前因为我的事而受处罚,他们都很怨恨我,我也因为他们配合邪恶迫害绑架妻子而怨恨他们,那天我感觉我一切怨恨都没有了,只有对众生的无限慈悲,他们也没有了怨恨,说我善良,真的象《洪吟二》〈法正乾坤〉讲的“慈悲能溶天地春”。
在被关洗脑班期间,同修都有这么个观点,不愿主动与“六一零”谈话,包括做所谓帮教工作的,在这方面我是这样悟的,旧势力希望我们消极承受,而正法就是正一切不正的,怎能由邪恶随意摆布。我就采取主动,天天找“六一零”、队部、所部讲道理,“六一零”受不了了,就把单位领导和公安找来,公安处长说对我实行监视居住。我说:“法律上对监视居住适应范围是居住城市而不关押场所,我不是犯罪嫌疑人,也没有诉讼程序,大法弟子是被迫害的,你们公安本身这样做就是违法。”他诬蔑大法。我告诉他们:“大法洪传,使人心向善,身体健康,于国于民都有百利而无一害,何来邪之理。用中共自己人大常委会定的适应邪教范畴六条,套在共产党身上条条合适(当时还没有《九评》)。”他们觉得理亏就说:“人家说你只有初中文化。”我说:“是的,你们都是大学生,为什么连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大法弟子都理论不过呢?因为大法是正确的,我站在正确的基点上怎么讲都是对的,你们站在错误的基点上去维护它的错,这永远是错的。”
二零零二年下半年是邪恶在关押场所迫害大法弟子最残酷的时候,洗脑班里的男同修们一起集体背经文、发正念、坚持晚上炼功,环境很宽松。我在洗脑班被关押一年后回单位上班。
同事都理解大法,愿意了解真相,过去长期监控我的党员也办了三退,有时开会觉得领导都没我讲得好,就叫我来讲,每次这样的机会我都抓紧跟他们讲邪恶为什么迫害大法,告诉人们大法的美好。作为大法弟子不管在任何环境都要证实法,讲清真相,那里的众生就会得救,环境就会变好,因为大法弟子是那里众生得救的希望。反之,如果同修因为各种原因不敢堂堂正正证实大法,我看那样的环境就恶劣,众生魔性也大。
二、做众多小花中的一朵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边的资料都是靠别的同修给的,我想买电脑,一说起电脑就头晕,连英文字母都搞不懂,自己又是挂了名的重点人物,在家做资料点行吗?通过学法,挖根自己,还是怕心,什么是挂了名的重点人物,这是邪恶讲的,能承认吗?
我买回电脑和打印机后,和妻子就从零开始,一点一点的学,先学会上网下载,每天坚持看明慧网文章,跟上正法進程,先学会打单张、小册子、刻光盘,慢慢学会做《九评》书。把周边的同修带动起来,每个家庭都能做,要多少做多少,在技术和资料选材上多交流。
刚开始发真相资料时,很害怕,走在街上心都跳,挑最容易放的信箱报箱放,做的有点经验了就進到楼道里发,从一楼做上去,当把光盘从门缝里塞進去时手在发抖,心跳得脚都发软,小孩看见我这样也害怕。为什么做救度众生这么神圣的事都那么害怕呢?是自己没有摆正基点,我们大法弟子是这台戏唱主角的,世人都是被救度的对像,做这么好的事都胆胆突突,不就等于承认旧势力了吗?其实说白了对大法还是信心不足。以后每次出去发真相资料时都先发正念,状态好了,师父就会引导我進出方便的小区,众生就象等着真相一样,有时去到楼梯里的铁门一拉自然就开,有时刚去到就有人开门下来,做起来就顺利多了,小孩也渐渐怕心小了,现在都很会配合了。派发的数量也多了,有一次,晚上在一个小区楼内发真相资料,刚拿出来往门缝放时,一下门打开了,对了个正着,以往就会不知所措的了,这次我很稳定,轻轻把资料收回用衣服遮住,她好象没看见一样出来了,我等她走了以后,问小孩害怕吗?他说刚才整个人就象飘起来一样,原来心态稳定,儿子也同样稳定。
虽然经历过十年迫害,我还有很多地方修得不好,和参加法会的同修对比,很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够,不敢向师父汇报,再加上只有初中文化,拿笔就感到千斤重,不知从哪写起,直到看到明慧网文章《如果师父在主席台坐着》,是啊,我们真修弟子随师正法走过很多珍贵的路,珍贵的事迹应该写出来,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慈悲救度,不辜负世人对我们的期盼。写得不好,请同修慈悲指正。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html/articles/2010/1/10/1137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