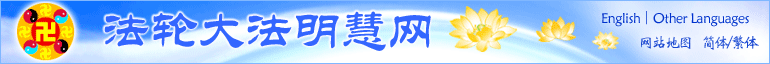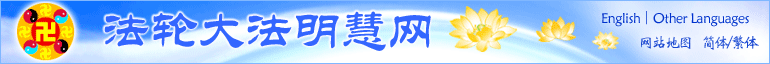|
【明慧网2004年3月14日】十六大期间的一天晚上,我正在街上行走,突然肩膀被一只手重重地抓住,扭头看到了一张凶巴巴的脸,旋即又冲过来几个大汉-----我遭绑架了。当来到一处场所时,恶徒们进屋就扒我衣服(它们第一想得到电话本,在车上没翻着,因为我没有)开搜,在场的小保安也配合。当时除了发正念,脑子里一片空白。当我只剩下胸罩和裤头时,恶徒说:“配合我们,咱们换一种方式谈怎么样?”见我不理它们,就拿电棍开电,边电边说:“我们就是你们说的恶警,这就是魔窟,就绑架你了怎么着?到这来不说也得说。”
虽然被电,因没害怕,所以我不觉得怎么难受。折腾了一阵子才让我穿上内衣,恶警又把我关进穿堂而过的另一间大屋的笼子里。大屋里关了20来人,我想这大概是个派出所。 恶徒们吃完饭把我弄到一间玻璃都破了的脏屋里,它们叫我脱衣服,我不脱,它们就动手,然后全身电,从脚电到嘴,电乳头、外阴;抓头发往墙上撞;用电棍猛击头顶数下,边打边说:“把你打傻得了,把你打傻得了…。。”然后还问“恨我们不?”他们假惺惺地给我喝矿泉水,见我不喝就灌,没灌进去就给我戴上背铐,把我推倒仰躺在地再灌。 一恶徒用嘴往我身上喷水,然后再电,还用胸罩给我擦弄脏的脸。见我还不屈服,恶徒们气急败坏地象走马灯似的窜来窜去,一恶徒穿着皮鞋照我头顶猛踢,我顿觉头晕,另一恶徒同时用打火机烧我的脚。我心里说:“师父啊,我不能死,救度众生还需要我,我是金刚之体。”这么一想头不晕了,恶徒也让我站起来了。后来恶徒的头儿来了,一看这样,气得拽下我一绺头发,然后抡起了胶皮棍狠狠地给了我一下子(被伤打的部位半年后才好),走了。 回到笼子里,恶徒把我双手反铐在笼子背对着20来个儿站着。看着泥乎乎的我,一个女孩儿哭了,边哭边说:“你真坚强,男的都难抗(第一次在隔壁打我时,他们都能听见)。”我就借机给他们讲真象。看人的小保安不让我讲,我也不理他,继续讲…忽然有人在身后向我提问,我作了解答。他说他是保安队长,对法轮功了解一些,电视演的他不信…我俩的对话使其他人明白了真象。 我问小保安抓我的是什么人?他说是国保处的。国保处是何机构我不知道,可它们穿便衣偷偷摸摸的行为完全是个黑社会。 第二天恶徒继续折磨我,折腾一会儿它们也觉得没意思了(从我被抓时起,一直在向它们劝善,其中一人对我的态度有明显的改变,再加上头天晚上电棍经常电它们自己,想去充电门开不开,里边难推,外边难进)。因为它们明白酷刑对我不起作用,一个说:“算了,要说早说了。”还对我说:“我们都比你岁数大,不该这样,谁叫你这么不听话?” 快半夜了把我带上警车,一路上它们唧唧喳喳,一会儿说:“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你活埋了。”一会儿它们把一些酷刑的招法说出来吓唬我。 看我不动心,一恶徒说:“你真行,你就是当代的刘胡兰、江姐。”我说:“刘胡兰、江姐她们有敌人,大法弟子没有敌人。”到了公安分局,分局不管;又去看守所,看守所不收。回到派出所已后半夜了,屋里只剩下两个人了。我心说:“我得走,不能进看守所,请师父帮助。”于是我发正念让那两人和保安睡觉…。两人很快睡了,保安却在地上溜达。我没急,继续发正念。一会儿保安坐下了,一会儿迷糊了…,我轻轻脱掉了一只手的手铐,把双手从笼子上抽下来,取下笼门上的锁头,推开笼门,轻手轻脚地来到保安身边,取下大门上的锁头,推开大门来到走廊。门岗没人,门岗边的屋里有一人趴在桌上睡觉。来到院里一看,一边是大铁门,跳出铁门就是大道;一边是一人多高的栅栏,那边好象是一个小区。我本应跳大铁门,因顾虑另一只手上有手铐,就想:“先到小区,等天亮了再走。”一念之差使我重落魔掌,因为那边不是小区。 天亮送我去看守所的路上,派出所的警察骂我笨,说我跑了与他们无关。这回走了后门,看守所才收下我。 一进牢房犯人就问:“是不是皮肤病啊?”我告诉她们是电棍电的。牢里有一个大法弟子,我跟她讲了经过,她看我难过的样子,劝我:“机会还会有的,你一定能出去。” 第一次非法提审我时,预审A问我:“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说:“怎么进来的?反正不是大风刮进来的,是黑社会绑架。”…后来A念记录时,回答大都是:“不语。”但当问:“身上的材料是不是你的?”答:“是。”我一听这是出了争斗心时让钻空子了。于是我说:“你重写吧。”没想到A一下就把记录给撕了。再重新问我什么我也不吭声,A知道上当了。 一次B提审我,没说多一会儿就开始骂大法,骂师父。我严肃地制止:“闭上你的嘴巴,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说啥。”B一下就跳了起来,“啪”一拍桌子:“什么?叫我闭嘴,办案这么多年,头一回有叫我闭嘴的,也不看看自己是谁?这是什么地方?从现在开始,不许你说话…。”嚷了不知多久,后来B问我话,我也不吱声,B嘟囔着:“你听我说评书哪,春节晚会怎么没叫你去呢?你比×××演得还好哪。”我说:“不是你叫我不说话的吗?”B说:“啊?在这等着哪,是你先让我闭嘴的。”一下气氛就缓和了。我跟B讲了骂大法、骂师父的后果,如果有机会去国外看看。B告诉我他2002年因公去了趟美国,在大西洋城著名的广场上看到了大法弟子炼功,场面非常祥和,B还说许多国家都让炼…听着听着我流泪了。 每一次提审,我都针对他们的心结讲真象,尽量去掉争斗心,所以他们还以为我的专业是老师呢。一次A说:“你们说真象大显,显一显我看看,看见了我就信。”我说:“如果发大水,等你看见浪尖了再跑还来得及吗?” 每次回牢房,我从不说谢谢管教。理解我们的管教不吱声,不好的就说我是哑巴。白天坐板时背能记住的法,晚上值班时炼一点动功,屋里虽然有两个监控器,但管教没管过。夜间值班挺辛苦,所以大家轮着来。为了子夜12点发正念,我主动要求长期值二班,到点叫醒其他同修。一天牢头看到了我刻在墙上的字,全屋8个法轮功,只有我有嫌疑。牢头问是不是我写的?我说:“你别问我”。于是她让犯人C用水把屋里的擦掉了,我没拦,很后悔。后风场上的没法擦,留下来了。为了此事,牢头报告了管教,并请求管教把我调走。过了些日子,因一点小事,C突然昏迷,正赶上非典时期,武警全副武装进了牢房,大夫楼上楼下地跑,简直象翻了天。好几个小时C才苏醒。一些犯人知道C是遭报了。后来我改变了方式,放风时拿布蘸水在放风场水泥地上写师父的诗,大家围着看,愿意学的就学,在屋里想学但怕牢头的,这下也有机会了。 为了把身体不合格的同修送去劳教,管教叫牢头偷着给菜里下药,我发现后告诉了同修,揭露了邪恶,气得牢头跟我喊叫。 管教找了个借口给我调了牢房,正巧当天晚上新闻联播播放陈福兆投毒杀人嫁祸法轮功。电视在上边演,我在下面大声讲真象,因刚来,不知道大家对法了解多少。但机不可失,大法弟子就应该对众生负责。闹闹哄哄地看完电视,牢头说该交电视钱了,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我举手说我不交。牢头找我谈话,她说:“电视它爱演就演,谁信哪?”我说:“你是不信,因为你接触法轮功多,知道真象,你问问刚进来的信不?”她没话了。我说:“本来迫害法轮功就是用电视、报纸造谣来毒害老百姓,电视都成了杀人凶器了,我交电视钱跟给杀人犯递刀子有啥区别?” 因这个屋就我一个法轮功学员,我就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因为刚被抓来的人,大都相信媒体的谎言,只有通过我的言行,她们才能逐步了解大法真象。一天我写完诗后,另一个D也要写,我们就一边说一边写…。突然放风场上空一声尖叫,抬头见是主管隔壁牢房的管教在喊我屋的管教。她们站在上面看了一会儿,然后我屋的管教罚了D。我找管教问:“D并没有违反监规,为什么罚她?”管教说:“我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但让别的管教看见了,我也没办法。”后来此事低调处理了,管教还让牢头转告我别多想。后来D学大法的劲头更足了。一位阿姨总焦急地问我:“出去怎么找你呀?” 当A第12次提我时,我猛醒了。虽然每次我都发正念指挥他们放了我,他们也说应该放我,可拖到现在也没放。我问A可以给领导写信吗?A说可以,并告诉我主管领导的姓氏。过了5天,上边委派B来问情况,我还是要求无条件释放。 一天午休时,迷迷糊糊就听喇叭里叫我收拾东西,许多人爬起来祝贺我,可我却没什么反应,因为那帮恶徒太能骗人了。我边收拾东西边发正念,出去一看真的是释放。 第二天上午8点多钟我来到看守所给同修送钱,遇到了一对老夫妻,他们唯一的女儿在牢里,也是大法弟子,被判了4年。看到他们伤心的样子,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多少幸福的家庭受迫害?多少大法弟子遭残害?而昨天的此时我还在层层铁门里。 300来个失去自由的日日夜夜过去了,有多少该我帮助的众生失去了机缘。虽然自始至终都在否定着邪恶的安排,尽量不消极承受,但因纯正的程度没达到标准,所以才造成拖拖拉拉。从以上的经历中我能看到:当自己心在法上时,环境就在变。我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都是师父在做,师父看我们修正自己、救度众生的那颗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