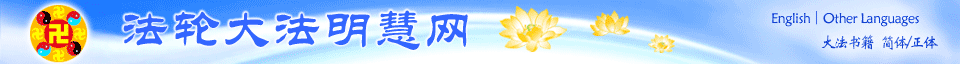【明慧网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刚到劳教所的那个夜晚,我是睡在操场上的。小院子里用简易的木竿挑着灯,夜深了,操场中有一排人不能睡觉,在那儿背“所规队纪”;工棚边上有一排人并排睡在木板上,很挤,人挨着人。值班把几个人弄醒,让她们挤紧些让出一个空儿好把我给塞进去。我躺下,看见上边撑着编织布象征性的遮着。这时是2000年底,已经初冬了,但因为宿舍不够住,新来的几十个人要睡在操场上。每天夜里等其他人回宿舍后搬床板铺地,早上提前起床收好,遇到下雨就把工棚里的台子挪开一些,然后在地上铺木板睡。这个工棚是用钢筋和铁柱搭起来的,顶上盖着石棉瓦,只有两面挨着围墙,另两面是空的,风雨随时可以飘进来。这个工棚平时要容纳一百多人干活。
到了白天发现劳教所到处都是人,因为人员严重超编,场所不胜负荷。我深深感到在人群中的寂寞,这里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罪恶、仇恨和背叛随处可见,一切让我窒息。我感到非常黑暗,好像邪恶有数不清层天的厚度,一起压下来。而此时正是广西第一劳教所女子大队的转化高峰,只有十来个大法学员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坚定修炼大法。
一进劳教所,强制洗脑就开始了。起初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很多人都转化了,其中有站长们和我熟悉的辅导员R。企图转化我的人们蜂拥而来,我花了3天时间了解并破解了荒谬的转化,观察到不少人在被关押中放不下生死,走向自欺欺人的邪悟。但是我却陷入两难的困境:确认了真理,却对坚持真理信心不足。我希望自己像金刚一样,挺过巨难,更有为法负责的想法。然而那时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难熬,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在回家的诱惑下,我想采取迂回的办法:玩个文字游戏吧,然后出去,再改回来。可这是一条背叛和毁灭的路:当我试着那样做的时候,只觉得从里到外所有的生命体全部死亡了,没有一线生机。我知道如果这样苟活下去,只是一具行尸走肉,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这样的人生虽有实无。我在心中说:再给自己一个生的机会吧!此念一出,立即行动否定了错误的行为。当晚劳教局的一位领导问我:法轮功好不好?我坚决的说:好!这一切只不过发生在一天24小时之中,但我犹如经历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生死决战,从此彻底否定了逃避和模棱两可的态度。
不久我被调去一个严酷的中队。我知道这是加大迫害,但表面原因是邪悟者在背叛大法以后人性扭曲,教唆恶警对我施压造成的。这些人有的是我的朋友,有的曾与我终日相处,了解我的弱点和缺点,认定我不能吃苦,就叫恶警把我弄到严厉和劳务重的中队,并一度企图封锁我的精神,不让我接触任何信息,只许看监规。
可是超负荷的劳动对我却是一个死关。因为在个人修炼中不扎实,炼功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旧势力看到了这一点就抓住不放,想要毁掉我,为此我大大吃了苦头,真是深刻的教训啊!那时还没有悟到全盘否定迫害,不应被动接受奴役。
劳务一般都做手工活,手、眼、心时时都要集中贯注在手中的活上,时间长了很多人的双手伤痕累累,时常缠着胶布。只做了一段时间我的手指就变形了,指头上曾磨出一个大脓包。任务永远完不成,如果完成了第二次就把任务定得更高。本来对劳教所国家有拨款,但劳教所为了多获利大量的揽活,靠奴役被劳教人员牟取暴利。一般找到的活都是短期批量性的,所以工期短,种类多,往往刚学会刚上手就要换一种新的活了,不好适应,还不时要赶工,很紧张。因为只能睡很少的觉,有时还要干通宵,以至哪怕只有十分钟、五分钟空闲时间,工作台上、凳子上、地板上就会趴着疲倦的人们。
我往往做到筋疲力尽也达不到定额,刚下中队时经常躲到工作台底下偷偷的哭。每天十几小时高强度的持续苦役,人就像一台机器麻木的不停的干着,对我来说很难承受 ,出去上厕所走出工段大门时往往两眼发黑,什么也看不清,只好跟着夹控走。吃饭时蹲在操场上,耳朵直鸣叫,各种感官都不灵敏,好像和周围被隔开在两个世界。完不成任务的受到多种惩罚,我曾被体罚、罚分、不得睡觉、不得洗澡等。有好几次实在太辛苦了,最后意识都不清楚了,知道自己活着,感到苦,心中只剩有一念:真善忍。
每次身体上的承受达到崩溃的边沿时,洗脑就会接踵而来,妄图让修炼者在不清醒的情况下邪悟。洗脑方式有强迫看诬陷、诽谤大法的录像、听所谓的讲课,还有就是邪悟者的所谓谈话等。来找我“谈话”的有上百人次吧,男队女队都有来的,甚至已经解教回家了的也来。每一次和他们交锋我都发现邪悟的荒谬破绽,每一次都从中证实大法的伟大与圆容不破,我好像踩着他们的肩膀往上走,越走越踏实。有时来的人多,有时来的人很邪,带的场不好,一来我就头晕,眼睛也有点睁不开。我就想,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我应该掌握主动权,就从法理上和他们谈。因为我并不落入他们的思维陷阱,而且道理上他们又讲不通,有两次有人无可奈何的哭了;还有的和我交流后明白过来了。最后恶警不敢轻易让人来找我谈话了。当时我还抱着人的念头:故意和一些邪悟得很严重的人谈话,使她没有时间去害其他学员。
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应该对劳教所的状况负责,不仅女队,还有男队,我们应该对整个宇宙负责,我们应该制约邪恶。这样想后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扩大到超出女队的范围,一直扩大到男队那边去。这段时间集中精力这样想的时候,我有很多次看到、感到劳教所的院墙、楼房坍塌下来,恶警队长被我的力量一次又一次的打倒,有时觉得它被消灭了。但有时倒下之后那个邪恶狂笑着又站起来,我又把它打倒,它又狂笑的起来,一次又一次的,次数太多了我就生出困惑,以为没起什么作用,就有点想放弃。而且当时师父还没有讲发正念的法。我看得也不清楚,好像在想象一样,我有时担心做错。我把这个想法和一位学员L交流后,她赞同了我这种制约邪恶的做法,此后我就一直坚定的这样做。 后来离开劳教所以后和L谈论当时的事情,她说我和她交流之后,她在一次点名时想着阻止行恶,看到自己另外空间的身体立起了右掌,当时只觉得奇怪,回来后看到经文才知道是发正念的手印。
在劳教所里,我还有另一个想法:我是水,谁也阻拦不了我。悟到之后,自己周围的环境就发生了改变:我比一般坚定修炼的学员更自由。别的学员被夹控看得很严,但我的两个夹控却不怎么管我。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个学员,她的夹控见我没有夹控跟着,以为我是被所谓转化的,就走到一边去,我趁机把经文《道法》背给了该学员。我就这样通过各种机会和方式和坚定的大法学员交流,在残酷的迫害中我们互相鼓励,一个眼神、一丝微笑都是无形的动力,大法把我们连在一起。
有一个夹控很邪恶,对我看得很紧,那时也是劳役最艰苦的日子。这时已到三伏天,工段变得像一个大火炉,一百多人的工段只有一个出口,没有窗户可以打开,只有几个电风扇,日夜亮着灯,人在其中很烦躁,还要专心的做手工活,我感到呼吸都困难。有几次我觉得过不去了,整个人好像随时都会崩溃而死掉,可是却又死不了,就那样煎熬着,好似永无尽头,感到真是“生不如死”啊。后来我想:如果大觉者处在我的位置会怎么样呢?宇宙的保卫者为了宇宙的安全可以跟魔同归于尽,那么如果为了宇宙的安全要永远在监狱里受苦,我想那些大觉者一定会毫不犹豫。那么我也要做到,无论如何也要做到。不久之后,我到四楼晒衣服时,抬眼望去远处的市区一幢高楼顶上赫然立着两个大字:封顶。我知道遭受的迫害已到顶了,果然没过多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慢慢的处境和劳务变得宽松。
R在解教前告诉我:她已醒悟了,她还要帮助更多的人。我一听就落下了眼泪,但是她没能回家,因为她传经文被发现了,邪恶之徒十分震惊,一个恶警说:“R,你给了我们沉重的打击!”当时劳教所的气氛十分紧张,两三天后R不见了,谣言四起,传说她被逮捕了,大家很难过。过后才知道这是邪恶之徒制造恐怖的手段,原来R被转到别的大队去了,并被延期几个月。
此时发正念的口诀传进来了,虽然误传为在四个正点发正念5分钟,但我已确认正念的作用。我在很多情况下都能控制局面,心里有一念:修到今天了,邪恶动不了我。有时跟恶警狭路相逢,一动念或者目光刚转过去,就感到背后的法器飞出去清除其背后的邪恶因素了。
我到劳教所大约半年后,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达到几百人之众,坚定的也有几十人之多了。其中不少人站出来反迫害,她们有的绝食、有的拒绝奴役劳动、有的点名不答到、有的不穿队服、坚持炼功等,没有统一的形式,每个人按照自己对法的理解做。恶警很恼怒,加大了对这些学员的迫害,但是她们的思想和言行就像金子一样,放射着真理的光辉。此时我感到了自己心性上的差距:求安逸的心重、有许多妥协的行为和错误言论、甚至还有因认识不到而配合了迫害。我很后悔以前没有精进,在个人修炼中没有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在心底里呼喊着:“师父,我要学法!我要出去!”与此同时,我悟到不应该被关着了。我对一位坚定的学员说:不要被关在这里,外面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又过了几个月,我的处境越来越宽松,心里明白这里已经关不住我了,该走了。经历过这一切我更坚定了,成熟了,邪恶之徒再也动摇不了我。以前那个不精进、不能够认真对待学法、放不下人的执著的我,通过认真的思考和实践,成为了一个坚定的修炼者。
最后我提前了将近一年出去,那时劳教所轰动了,此前恶警一直吓唬说不转化不放人。
我最终冲破了监狱的束缚,怀着对大法更深的理解和坚信,投入了证实法、讲真象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