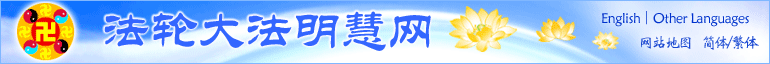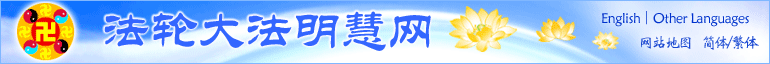|
【明慧网2004年1月13日】我以前患有多种疾病,过敏性哮喘、类风湿、腰疼、神经衰弱、失眠、神经性头疼、耳聋、咽炎、喊脾肿大、胃下垂、十二指肠球状溃疡、眼睛高度散光,到最后生活几乎不能自理。直到97年,我遇到高德大法《转法轮》,我一口气看完,觉得这就是我一生中在寻找的,因此义无反顾的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全身疾病不翼而飞,更加深了我修炼大法的信心。
上访北京 99年7月20日,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开始了对法轮大法的打压。这天早上,我和我母亲同时被绑架,母亲不知被绑架到什么地方。都昌派出所所长张言超、恶警马涛、治安股一个50多岁的男的,还有我单位的几个人来劫持我。因我不上车跟它们走,它们5、6个人用拳打、捣、拖、抬,硬塞进车里,拉到了周子地毯厂楼底关起来,因我不听它们摆布,有二人强行连拖带打,把我拖回房间。有一女恶警刚从警校毕业,她用拳捣我。我想上厕所,走到门口处,他们就用拳和巴掌把我打回房间里,甚至不准我靠近门口,我身边有两个人看管。在门口处,有4个男警察,楼梯还有值班的,在大约早上4点左右,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从他们眼皮底下正念闯出,就这样我又踏上了上北京正法之路。 在我走到天津时,被天津分局截住,关在分局的大院里,那里面已经关了有一百多个大法弟子,恶警挨个询问我们的姓名,我没说我是哪里的人,那时只有一念,我不能配合邪恶,因此不知为什么它们把我漏掉了没记。晚上,我们大家在一起背法、炼功。到了7月22日下午2-3点钟左右,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取缔法轮功的非法决定,刚一宣布,马上就有一个恶警把一个站着的男大法弟子一拳打倒在地,然后又上去7、8个连踢带跺,打昏后,就不知拖到什么地方去了,其中一个恶警头目说:“看到了吧,这就是下场,谁要再炼,再提任何条件,他就是例子。”过了一段时间,各地来车准备接人,那些不想走的大法弟子,它们抬、打、拖,有的衣服都被拖破,裤子也被拖了下来,我随着烟台的同修上了车,它们让我们自己拿钱买车票,押着我们上了火车,走到半路,我们几个同修商量了一下,说不能回去。因为大法已遭到了恶毒的攻击,作为我们大法弟子都应该捍卫大法、证实大法,想到这里,我们决定继续进京上访。 无论怎么迫害,绝不妥协 我们到北京几天后,我又被昌邑市公安局劫持回当地,它们审问我在北京到底干了什么事,为什么上北京。我说:“政府非法迫害法轮功,非法绑架我和母亲,我知道在当地告诉你们不管用,我又看到政府在电视上非法取缔法轮功,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随便取缔,因此我觉得更有理由进京上访,好让中央知道真象,希望你们和国家领导允许我们学法炼功,恢复俺师父名誉。”它们又问我去北京往回传经文的事,是谁给你的。我不说,它们就打我的头,不让睡觉,罚站,我昏倒在地,它们也不管,就让我躺在地上。当时迫害我的是四个恶警,马涛、王淑华(户籍员),还有治安股的一个恶人,还有一个后调入市看守所继续迫害大法弟子。5天后,它们把我非法送进了拘留所,扣了我3000元钱。在拘留所,恶警逼我写“保证书”,我不写,他们(公安局)让我单位的人作担保,逼我父亲写“保证书”,说我父亲没看好孩子,我父亲就责问公安局的人,“你们是干什么的?”第7天把我放出来后,公安局、派出所,天天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在家。 99年10月份左右,我又被公安局长张树增骗进了拘留所。我问拘留所所长,是怎么回事。他说:“你上回执行期(指非法关押)没执行完,这回正好补齐”。我一听简直是不讲理,我对他说:“说关就关,说抓就抓,难道做好人也错了吗?”他被问的无话可说。我想公安局执法犯法,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在10月1日,它们放我回家,10月6日,我又踏上了去北京的车,我想讨个公道,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让我们有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结果我刚进北京住旅馆,就被潍坊驻京办事处的人绑架了回来。第二天,当地公安来了11个人,给我们每个人戴上手铐,把我们当地7个人劫持回当地。到了当地公安局大院的台阶上,站着三四十个警察,其中一个念着我们的名字,然后马上就有4、5个警察一组把我们带走了,我被三男一女带进了看守所的审讯室,其中那女的搜了我的身。这个女恶警从“7.20”开始一直就充当邪恶的爪牙,搜完身后,就把我铐在铁椅子上。脚上带上脚镣,胸前有一铁板,使劲的顶着前胸,两只胳膊在铁椅子的两侧,每只手上有两个铐子使劲铐在铁椅子的腿上,铐子都嵌在肉里面,是弯不下腰,稍微一弯腰,前面铁板顶着胸部就喘不上气来,直起腰来手和胳膊被铐子拽得疼痛难忍。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手和胳膊、脖子、背、腰疼痛难忍,就这姿势一直长达15个小时,简直就是非人的折磨。因我什么也不说,它们又给我上背铐,这种刑罚更残酷,没几秒钟,胳膊手腕就像过电一样,奇痛无比,痛的我马上出了一身冷汗,眼前直冒金星,接着就开始呕吐,我一两天一夜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但也不感觉饿,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力,才使我能在这样残酷的迫害下仍能挺住。大约过了5小时,它们看我实在是不行了,就把我放下来,又铐在铁椅子上(刚才所说的那种酷刑)。 当时我的手和胳膊已经失去知觉。这时,我才看到我的手已被铐子勒的破了皮,手背肿了有二寸厚,就这样一直在铁椅子上铐了我五天,身体遭受了非人想象的痛苦。晚上不准睡觉,刚一闭眼,当时刑警大队副队长就说,“你再闭眼就用火柴棍把你的眼皮撑起来。”在这期间也不准我上厕所,一个姓焦的邪恶之徒说:“拉下尿下,你自己再舔干净。”当公安局的人知道我非常坚定后,当时的刑警大队指导员向局长报告,局长亲自来审讯我,我当时一直想着师父讲的“生无所求,死不惜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洪吟》“无存”)最后邪恶们也没能从我嘴里问出什么来,第5天就把我劫持进了市看守所。 在昌邑看守所一月后,因我一直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在本地看守所对我没有什么招了,又把我送到一个最邪恶、最残忍的看守所——潍坊寒亭看守所,在寒亭看守所我遭到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在这期间,因我和另一个同修炼功讲真象,恶警们把我们两只手用铐子吊在门上脚尖着地,脚后跟抬起,吊了有7、8个小时,另一同修昏了过去,才把我们俩放了下来,放下来后,我的两只胳膊已经不能动弹,到了第三天才恢复知觉,当时想,无论邪恶怎么迫害,绝不能向邪恶妥协,同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转法轮》)。 40斤重镣铐加身 我们俩又继续炼功,恶警就用几十斤重的铁镣,把我们俩连在一起,就是把我的右手右脚和另一同修的左手左脚紧紧靠在一起,大弯着腰不能直腰,她动我必须也动,睡觉时我们俩人就象“对虾”一样弓着身子,不能翻身不能动,因一动互相就被铁镣拽的手脚特别痛。几天后,恶警问我俩还炼不炼,我俩说炼,就继续给我俩带了半个月后才卸下来。因那个同修要走,当时那个所长让我坐在地上把腿伸直,手必须拿着脚尖,并且大声审问我“为什么来这里”,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为什么来这里我不知道,也不知我犯了什么罪。”那所长说我嘴硬,气得他哇哇直叫,干吼也没办法,就又把我关进监视。在这期间我继续炼功、讲真象。邪恶见我继续炼功就更加残酷的迫害我,就又给我戴上一重40斤重不能直腰的大铁镣,光铁链子就一大堆,手和脚紧挨在一起,躺不能躺,坐着都躬着身子,头紧靠在膝盖上,带这种铁镣,大小便必须由另一监室的人侍候,不能自理。不到一天,手和脚肿的很痛,皮也磨破了,监室的另一人也害怕了,怕我有什么意外,就打报告要求他们给我卸下来,但他们不给我卸,只是给松了一个扣,但还是直不起腰,就这样一直带了20多天,因带的时间太长,铐子已经铐死,用钥匙都打不开了。后来一个犯人让我坐在地上,用大锤子才把脚上的镣子砸开。 电棍突然没电了 因我一直坚信真善忍,三个月后我被送进济南第一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在那里,我被分到第四大队严管,刚一到第四大队,一个姓王的女恶警,他迫害我们大法弟子是最积极,也是手段最邪恶的一个。又把我分到第二大队,因我坚持炼功,讲真象,到了晚上只要我炼功,二大队杨队长就让犯人打我,抓我的头发往铁床上撞,嘴也被打得流出了血,后来,只要我们一炼功。他们就叫犯人把我们用绳子绑起来,先把两只手用绳子紧紧缠住,再把脚用绳子缠紧,然后把两只手从头顶向背部挂,与两只脚紧紧挂在一起,肚子贴着床成弓箭形,大约不到半小时,手和脚就开始痛,因手脚血脉不能流通,不一会就变为青紫,一绑就是一夜,有8个小时。 早上起床提前半个小时给松开,因为还得让你干活,因绑的时间太长,手和脚都肿的老高。后来恶警对炼功的人员用电棍电,每天晚上都听到电棍电人的声音,弄的整个大队阴森可怕,后来我一直在劳教所的月小结写上洪法文章,它们就用电棍电我,叫我必须照他们要求的格式写,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不能违背我的良心。”当时迫害我的恶警有:曹燕华、孙娟,它们两只电棍轮着电我小臂,刚一碰上就闻到皮肉烧焦的味道,我一看小臂像蜂窝一样都肿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电棍突然没电了。孙娟就捂着肚子说肚子痛,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力。孙娟也感到奇怪,充了一夜电,怎么会没电了呢?结果孙娟用手一试,狠狠的电了它一下,但再也没电我,我觉得它们也挺可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