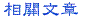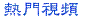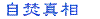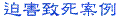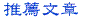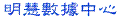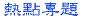四川会理县胡泽聪自述被迫害的经历
我叫胡泽聪,修炼法轮功以前,我患多种疾病:风湿痛、手不能拿筷子、脚不能走路、哮喘病曾经使我昏死过几次,到医院输氧才抢救过来,后来中西医治疗都无效,钱花了不少,生活不能自理,我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一九九八年,经亲友介绍,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才一个月,我全身的病状就消失了,从此我象换了个人一样,一天种地、做家务、带孙子全都能干,身体轻松了,心情也愉快,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给我家庭带来幸福。
多次被非法拘留、关押
二零零零年三月,有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信访办,我也签了个名,就为这事,公安局一科杨绍亮带人反把我绑架到红旗派出所“审讯”,接着又非法拘留我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九月,我县法轮功学员到县政府,准备向政府人员说明我们是一群做好人的人,修真善忍没有错。结果被公安局一科罚款二百元。收据上经手人是李永坤。从那以后乡政府经常派人来家威胁,不准炼功,不准外出。
二零零一年一月,我因讲真相被人构陷,清早五、六个人闯进我家,到处乱翻,没搜到什么东西,就把我绑架到派出所,折腾到下午又非法关进拘留所,一关就是半年,还让我给所里做饭,洗菜,喂猪。
六月十二日,一科俞明刚拿劳教书,让我签字,我说:不会签。他就代签了,说要劳教我一年半。然后也没通知家属,就把我送到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在劳教所我旧病复发,一个多月后,劳教所怕我死里头,承担责任,我被放回家。
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我在顺城东路的一条小巷发真相资料,被祁顺华和其儿子打电话构陷。一会儿,国保大队的杨绍亮带来两个警察把我绑架到公安局,国保队成员温晓红问我:资料哪来的?我没回答。他们就去抄我家,抢走了家人很多私人物品。然后,将我关进看守所,第二天,温晓红又来问我资料的来源,见问不出结果,她走了。又过了几天,来了几个我不认识的人,他们说我被判刑了,问同不同意?我说:不同意。他们说:同不同意,都要签字,他们才能交差。
大概过了半个月,一天晚上,我突然呼吸困难,折腾到凌晨三点,所长秦世君看我很严重,怕承担责任,才喊了几个人送我到县人民医院。第二天一早,他们喊来我女儿、女婿要他们去付我的医药费,我女婿说:人进所这么长时间,我们都不知道现在变成这样了,我们也管不了,就拉女儿走。所长秦某又让人叫我儿媳去办手续,并叫交一千至一千五百元钱。儿媳说家里困难拿不出,他们又让我老伴拿钱,老伴也没拿,无奈只好放我回家。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日,我和法轮功学员准备到邻县去发光碟,当我们乘坐的班车到我县与邻县交界时,司机接到一个电话,班车就停下了。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不一会,城北派出所警车就追来了,他们将我们绑架到城北派出所,又打电话。一会儿,国保大队江丰良,温晓红,刘建平和另有一人,他们非法搜身,把我们带的资料和光盘全拿走,并追问资料哪来的?我说:我不会说的,省得你们会迫害别人。江丰良说:“不是迫害,是挽救。”他见问不出啥,就把法轮功学员和我非法关进看守所。
第二天,我儿子到看守所去问,里面的人说我没在那里,过了十多天国保的和送拘留的才送通知书到我家,见大人都不在,就让我十四岁的孙女签字,家人才知道我确实在狱中(通知书上有办案人江丰良的签名)。在看守所呆了一月,我们被转到拘留所,才知道法轮功学员罗继平被劳教一年半,我被劳教二年。四月十九日中午,我从床上摔下,所长启兴友叫狱医给我检查,他说没什么。直到晚上十点,他们见我一直吐,一直咳,只好送县医院,医生说是哮喘病发作。启兴友问医生:能否住医院?医生说:没床位。我听后赶快表示我家没钱,无奈他们只好又拉我回拘留所。
过了几天我女儿、儿媳听到我的情况后就去看我,当时我是由同监室的两个人架着出来的,我呼吸困难,说不出话,所里警察张德琼见状忙说:缺乏营养,判了刑又不送走,人变成这样,不是他们的责任。让女儿、儿媳去找公安局说情况。二十九日,在儿女们强烈要求下,交了三百五元钱,说是检查费,才叫他们带我回家。
再次遭绑架 被送楠木寺劳教所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一日晚,拘留所所长启兴友带了三个人到我家,看见楼上有灯,就上去找我,看我不在,就走了。第二天又去找我也没找到,听邻居说他们去了好几次,还一天出三十元钱让隔壁的监视我,看我回家就打电话给他们。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二点左右,我在法轮功学员家,国保大队杨绍亮、江丰良、温晓红等七、八人将我绑架到拘留所。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六日,女狱警张德琼用手铐铐住我往楠木寺劳教所送,一路上我都在吐,什么都吃不下。中途住了一晚,他们还把我铐在床上。到了资中楠木寺劳教所,他们把我架到三楼上体检,启兴友对医生说我是晕车,在家我什么活都能干,医生让他们留下五百元输液就交差了,而我就被扔进了劳教所这个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魔窟。
在楠木寺劳教所,他们让杂案犯人逼着我写“三书”,我说:不识字。就让被“转化”人员徐晓兰(音)代我写,并强迫按手印。
由于里面生活环境、条件极差,思想压力大,我病状越来越重。一天甚至出现几次危险,把他们都搞烦了,为了不担责任,他们给我办了“保外就医”手续,并通知家人。
十月底,我家人为办接我的手续,从县委找到公安局、派出所,他们一个部门推一个部门,就是不接人,也不办手续。直到十二月,家人自己到劳教所,劳教所见我病况无一点好转,就同意家人接我回来。
二零零九年四月,有一天,楠木寺劳教所有人打电话给我女儿说,我回家后,还到处窜,还去法院旁听(法轮功学员被判刑,我去听了)并威胁女儿说是她给我作的担保。我女儿问她是谁,她不说。
我修炼法轮功,身体好了,心情舒畅,还能帮助家庭料理家务,减轻了儿女的精神和经济负担;而中共邪党却不要老百姓过好日子,多次的迫害我,给我和家庭带来严重的精神和经济损失,这笔债中共和参与迫害者是要偿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