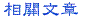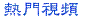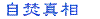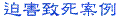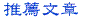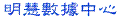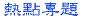湖北麻城法轮功学员杨玉峰遭迫害经历
 湖北麻城 |
下面是杨玉峰诉述她这十二年来所遭受的一些迫害。
一九九九年腊月二十,白果派出所把我送到麻城拘留所关了九天,传信叫我公公、婆婆交五千元保证金,没有票据,腊月三十放出。
我很困惑,这么好的功法,一定要炼。二零零零年正月初八,到当地派出所、政府综治办工作的有关负责人讲修炼的好处,希望政府能理解我们,给我们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
正月一十七晚七点多,派出所把我抓到当地敬老院,一群地痞、小混混在院里晃来晃去;一进去看见几个法轮功学员被强制面壁罚站,没有椅子,有几捆稻草,我就坐在稻草上。一群地痞、小混混叫我出去,强迫下跪,按倒在地。一会儿转到派出所,恶警刘、邱等拳脚相加,打的鼻流鲜血,双腿踢得青一块紫一块。一会儿强制赤脚下跪,一会儿冷水灌颈,冻的全身发抖。还有电棍逼供,恶警一边提审一边折磨。
直到天快亮,一恶警困了,强力睁眼瞅瞅我说:你怎么象个菩萨?自言自语的。刘姓恶警强制我抱着水泥柱子铐了一天。一天没吃饭,没喝水,没睡觉。下午五点钟左右丁朋成两次将我踢倒在地,那时两手戴着手铐起来困难。
晚上送进看守所,这一关就是近八个月。四月份,孩子父亲说派出所有人扬言要封我们的房子,提出要离婚。当我在难中,蒙冤枉受迫害,需要亲人关心和问候,他却落井下石,我的心感到拳头大的一团冷气,冰凉冰凉的。这大概是心寒的体会吧。在谎言的欺骗下,我把房子的产权给了他,忍痛将孩子给他抚养。 从此我没有家,也没有栖身之处。
五月份,看守所吃的青菜里有大青虫,咸菜里有大白蛆,白花菜里有卫生纸片、蜘蛛网,半生半熟的饭里夹杂着沙子。渐渐的没有食欲,头昏、惊恐、眼睛发红、睡不安神,象要疯狂似的怕人吵闹。度日如年,一时一刻都在痛苦中煎熬,渐渐的精神恍惚,手足麻木,酸软无力,一桶水提不起来。后来手痛的拿笔写字就写不好,头发脱落,白发渐生,幻想自己要长双翅膀飞出去多好。
六月份,手足由麻木变得疼痛象针刺,疼痛的全身发抖,听到送饭车来了,恶心想吐,心惊肉跳。后来洗脸拧不干毛巾,梳头手握不住梳子。加上肉体上疼痛,度日如年一点也不夸张。原来一百四十多斤的我,被折磨得瘦成皮包骨,走路摇摇晃晃。
九月三日放回,几个邻居大姐看到我,眼泪唰唰下落。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在家调养了二个月,疼痛渐好,手足麻木未好,行动不方便。彭、邱等恶警轮番监视我后,把我强行送到武汉狮子山戒毒所,大约十多天转送沙洋劳教所,一关就是度过二个除夕年。
在沙洋劳教所里,那里的管教干部指使吸毒人员刁难、打骂、折磨法轮功学员。在那里饮食、起住行动、说话都受到限制。一天下雨,上午挑土、挑砖,双腿麻木、行动不方便,摔了一跤,吸毒人员骂我装麻,叫我跑快一点,可双腿跑不快,湿衣服穿到天黑。收工时杨队长还批评我没有完成任务。
身体上、精神上的折磨,胸闷脑胀,烦躁易怒,每个月体检血压高。有一天龚恶警威胁说必须骂法轮功才能出去,我马上晕头转向,恶心呕吐,心脏几乎气绝,立即送医院抢救抽血几次,血一出来就凝固,输氧一个晚上。打四瓶点滴。
二零零二年正月从劳教所回家。二零零四年六月被中共恶徒丁朋成、刘世发强行抬到车上,绑架到洪山监狱附近度假村洗脑班迫害,做了一个法轮功学员不该做的事,从此而消沉,惊恐不安,这一状态持续了三年多,那阴影至今还有。
二零一零年五月去广州照看儿子,在火车上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徐州乘警发现,带到徐州公安局,将讲真相的碟子、传单、真相币、大法书、手机等扣留。非法审问后送拘留所,拘留所体检血压高,又请徐州医院专家确诊血压高,拘留所不收,转徐州医院住两天,三个恶警送到麻城拘留所又关了十五天,于六月四日放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