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选登| 关键时刻神念醒
初次运用神足通
我第一次运用神通的时候是在零一年的秋天。那段时间我和同修一起挂横幅,大面积发放大法真相资料,一时间真相资料几乎铺遍了市内的大街小巷。百姓们开始怀疑中共媒体对法轮功的揭批和宣传是不是造谣诽谤,中共邪党公安人员害怕了。紧接着,市区主要路口和居民小区平添了许多警察和便衣。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也被邪恶盯上了。
一天晚上,我和同修五姐刚从一同修家出来,就发现隔着小区铁栅栏围墙,有俩人直盯着我们,我俩快走他俩也快走。走到一个栅栏出口处,我和五姐分别朝两个方向走,这时跟踪者也分成两路追过来。我急忙往家赶,听到身后急促的脚步声,我的心怦怦跳的快要到嗓子眼儿了。情急中我想起了“神足通”,就在心里说:你追不上我,我用神足通。果然那人在身后只差一步就能伸手抓到我,却好象被隔着一层空间一样,他干着急够不着。我提前与本单元电子门沟通:快给我开门。结果走到跟前,没用我拿钥匙,电子门自动打开了。我刚進楼里,那人就追过来。我一边快速关门一边对它说:别叫他進来,拦住他!快速上楼的时候,我听到那人通过对讲门铃央求几户人家给他开门,只听到有人问话,就是没人开门。
進家后,我随手关掉电灯,站在门口听动静。不一会儿,听到一男子上楼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那人在对门儿和我家门口徘徊一阵子,才慢腾腾的下楼去了。这时五姐来电话说她刚才听到跟踪者衣兜里手铐声“哗啦”响,但最终也甩开他,平安到家了。
那时我是新学员,还缺少智慧,不懂得那种情况下不应该直接回家。但这件事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学大法的人跟常人真是不一样,如果不学大法,那天的我一定是插翅难逃了。我从此更相信大法书中提到的各种功能了。
神念令警察“向后转”
零一年深秋的一个早上,俩同修来到我家。刚说几句话,我的心一阵阵冷战,那种感觉就好象马上要大祸临头了。于是催促同修快离开,否则就来不及了。同修走后,我简单收拾一下也出了家门。刚下一层楼,就听到楼外面嘈杂的声音。透过楼道窗户往外看:一帮警察在那儿嚷嚷着,已经围在我家单元门外了,其中还有曾经来过我家的人。正想着是不是冲我来的,楼道里進来俩警察,我转身就往楼上走。走到家门口,正准备拿钥匙,忽然想到:不对呀,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学法轮大法的。“世间大罗汉 神鬼惧十分”(《洪吟》〈威德〉)。到底谁怕谁呀?于是我又转身下楼,大大方方往下走。下到二楼时,看到俩警察正准备上楼呢。我直视着他们继续往前走,没想到他俩根本不瞅我,嘴里嘟囔着:是不是这个单元哪?别弄错了,还是再问问吧。说着竟然掉头往回走,出门后问一位老人:这儿有没有谁谁呀?老人连声说,没有没有,你们到别处打听吧。听到没有说话声了,我便推开楼门,只见门外坐着一位邻居老大爷。大爷悄声说:快走吧,他们是来抓你的,被我支走了。
原以为他们走远了,我开门走出来。没想到,我用眼睛余光看到六个警察就在隔壁单元门外站着呢。可是我已出了大门,想躲也来不及了。于是立刻心生强大的一念:向后转!随着一念的发出,我忘了害怕,反倒转身看他们,谁知六个警察真的向后转,象排练队形一样齐刷刷的背对着我,自然没有发现我。我立即想到用功能“定”住警察别回身!就在我快速朝反方向走的时候,听到一个警察按响了电子门铃,问一户人家:这里有某某吗?门铃里传来对方不耐烦的声音——“不知道”,警察又按响了另一家的门铃。就这样,我听着他们的说话声,在他们眼皮底下堂堂正正的走脱了。
我先来到哥家,刚進屋,哥从单位打来电话。说警察去我家敲门好长时间,之后去哥单位诱骗他说出我去哪里了,哥很智慧的把他们打发走了。后来邻居说:我刚离开本小区,警察就说他们上当了,好象刚才没弄错我家的住址,于是又去我家敲门。
这件事对我不修炼的家人和邻居都有很大的震动,他们说学法轮功的人在刀尖儿上走都没事。当然此事对我震撼是最大的,我更坚信学大法的人有神通了。
运用功能反迫害
零二年四月中旬,当地中共不法人员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一群恶警把我绑架到看守所,我一進去就绝食,看守所长领着狱医和七八个警察,对我進行了野蛮的灌食。在郑姓所长的唆使下,一帮人如狼似虎把我按在地上。有人捏鼻子,有人按胳膊、四个警察分别跪在我两条腿上,他们使用开口器,把连着漏斗的液化气管子插入我的食道里,将大量药物和小半瓶大粒盐倒入漏斗里,再用凉水往下冲。一邹姓女恶警用皮鞋踩住我的头,大声吆喝着“灌”。我被憋得透不过气来,痛苦挣扎已不能唤醒恶警泯灭的良知。眼见半盆浓盐水被灌進体内,我也要窒息了。就在我感觉只剩一口气的时候,出于生命自救的本能,我想到立刻用强大的功能把盐水“返”出去,并在心里求师父救我。霎时间,隔着管子和漏斗,我大口往外喷盐水,盐水飞溅到恶警身上。看得出他们好象受了很大刺激,立即拔掉管子,转身出去了。
看守所长命令警察拿来十八斤重的脚镣把我铐在地环上。我便发一念:用功能把灌進我体内的药物都返到他身上!结果他刚走出监号,我和同修就听到他在走廊里呕吐的声音。
他们全都走了,我也不由自主的吐了半盆水,水里有血丝,还有飞蛾和做针线活儿用的线头儿,我知道是自己的功能把坏东西推出去了。一同修哭着问我能行吗?我感慨的说:我能行!于是背诵师父的话:“造就一个人、一个生命,在极微观下已经构成了他特定的生命成份、他的本质。”(《转法轮》)同修和刑事犯人都哭了。
不一会儿我睡着了,醒来时心里热乎乎的,感觉浑身哪儿都不难受了。我跟同修说梦见师父来看我了:在梦里,我是一个小男孩儿,被坏人关進笼子里不能吃饭。师父抚摸着我的头安慰我一些话,并给我送来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里面是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素馅儿,鲜香好吃极了……。醒来后我已记不清师父跟我说的话,只是感动的眼里含着泪,同修们听了也很受鼓舞。
当天一名同修说,警察在盐水里偷着下了泻药,目地是想迫使我屈服。同修说我一定会拉肚子。我立刻打出一念:我用功能把“它”闭塞掉!结果呢,我被铐在地环上,八天八宿都“没事儿”,我也没屈服。
后来几天里,恶警加大药量和粒盐,又灌我好几次,企图逼我要水喝,我坚决抵制!最神奇的是,师父赐予的一盘饺子能让我八天不渴也不饿,在我绝食绝水的八天里,身体一点都不难受。我深切感受到师父无时无刻的呵护,更加坚信大法的无所不能。
关闭狱中监视器
零三年,我在中共邪党的劳教所里遭受迫害的时候,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分插在两个大队。得知另一大队的同修无法看到师父的经文,我想出了办法,就要求劳教所大队长每天至少给我们一小时午睡的时间。而这时间只能从劳动时间里挤,这样两个大队必须在同一时间开饭,才能节省时间为劳教所“创收”。我知道他们宁肯让两个大队合在一起开饭,也不会放过剥削大法弟子为劳教所谋财的可能。于是每天开饭的时间也成了我给同修传递经文的契机。
一天傍晚,我换上一套米色迷彩服去了食堂,立刻引起另一大队同修们的注意,因为那套衣服是我在那里传递经文专用的。然而警察对我看得很紧,想接近同修都很难。怎么办?眼见那边的同修眼巴巴的瞅着我,我心里很难受。于是边吃饭边发正念,并想着用神通把食堂的灯管儿关闭掉,想着我能在混乱中把师父的讲法传递给同修。吃饭的时候,每瞅一眼对面的同修,都发现她们在看我,等候着我有所行动。我知道只要我一动,她们就会马上动。于是我把事先用塑料袋包好的师父的新讲法包在一个干净的笼布里,起身就往水房走。
队长发现了,大声喊着让我站住,我说我要去喝水,她叫喊着让别人给我拿。我没理她,照常走,队长追过来。这时对面的同修也在那边往水房方向走。我边走边对灯管儿发出强大的一念:灭!并求师父加持我。真就象闪电那么快,八个灯管儿瞬间全灭了。食堂里叫的叫喊的喊,二百多人乱作一团,队长也忘了跟踪我,大声喊着都别慌,都在原地不许动!然而我和对面的同修没有去水房,而是默契的都往食堂中间走,就在擦肩而过中,我把笼布递到她手里。刚递完大约几秒钟,灯管儿自动闪了两下又亮了。队长喊着没事了,刚才肯定是电源短路了。我和对面的同修都已回到饭桌前,两个大队二十多个不“转化”的同修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家感慨的同时,相互对视着会心的笑了……
亲眼目睹了劳教所恶警在很多方面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我想到用写检举信的方式曝光、揭露邪恶。然而劳教所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严密监视,一个小号里至少有两个“包夹”日夜看守着,怎么有机会写呢?
我先用几天的时间发正念清理空间场,然后想到用功能。我用强大的意念打出功能,先把室内头上的监控器关闭掉;再用“定功”将同室的两个邪恶“包夹”定住——定其整宿烂睡如泥;又发正念让走廊里值夜班的人疲惫不堪睡过去,让她们一宿不掀门帘窥视我们的房间。这样想了半个小时,便听到两个“包夹”鼾声如雷。我当时直想笑,心想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女人这样大声的打呼噜,替她们脸红的同时更感慨功能的作用。
于是犹如進入无人之地,我开始写信了。写的过程中,不忘求师父保护和加持。因为是就寝时间,我只好躺在床上侧卧着身体写。一种姿势写累了,再翻身换一种姿势。那一宿,走廊里值班的人真就没有一个掀门帘窥视的,有时候我还能听到她们的鼾声呢。那一宿,我仿佛進入到另一个空间,一个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空间,随便想干什么都可以。
天亮了我也写完了。白天的时候,听到俩“包夹”和走廊里值夜班的人唠闲嗑。都说自己从来没有睡过那么长时间,又说好象被什么给“定”住了,就是醒不过来。欣慰的同时,我在心里默默感恩师尊的加持。
次日上午,与我同住一室的一名同修获释回家,我让同修把信带走了。同修很快把检举信寄给本省劳教局,半月后,劳教局派人到该劳教所检查核实。尽管有“内线”提前通风报信,劳教所事先做好了伪装。终究天意不可违,在食堂伙食、小卖店食品价格和保质期等方面被查出破绽,劳教所不得不在伙食方面作出调整,这样全所几百名劳教人员和法轮功学员总算能吃到馒头和一些蔬菜了。而且小卖店里的食品也不都是过期的了。
解体邪恶出魔窟
在劳教所,恶警把我关小号,十多个洗脑帮凶天天轮番围攻我。可笑的是,她们的谬论根本不堪一击,没有人能够动摇我。半年多不“转化”,恶警把我关在劳教所最冷的监号里,暖气全卸掉,窗户和墙角都是冰。我知道无论面对怎样邪恶的迫害,都不会被“转化”。可是一進这监号,穿多厚都被冻的直打颤,不免还是很心酸。
又被围攻九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实在困极了,就强眯了一会儿,刚睡着就听见漫天的歌声,只听到四句就醒了。正感慨师父用歌声鼓舞我,忽见床边墙上闪金光。我坐起来看,原来石灰墙壁上刻着方方正正的两个字:“坚定”!我顿时流泪了,再不觉的冷和苦。我在心里说:师父啊,弟子一定从这里走出去!
随着天天背法,法理不断的启悟我。我悟到即便按旧宇宙的理,我也该回家了,邪恶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关押我。可是怎么回呢?于是求师父救我出魔窟。当晚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坟丘一样的土堆上,津津有味的吃着烧饼和香肠。偶然间一低头,发现自己竟然是站在垃圾堆上,再仔细看,原来烧饼和香肠也都是用垃圾加工的。我再也不想吃了……醒来后我悟到,劳教所好比垃圾堆,什么人都有,大法弟子不该呆在这里,这是师父点化我通过绝食走出去。
我绝食四天后警察才发现,队长找谈话,软硬兼施都没能吓倒我。后来我想起师父说过旧势力对每个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它们的东西。我就想:一套不就是一个系统吗?是不是一个人被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哪个监狱哪个劳教所迫害,也都是它们久远以前安排好的呢?那么我被它们安排的这套迫害系统中就有这个省这个市的这个劳教所,以及这个劳教所里的这个大队、这个小号?于是我对着劳教所的整个空间场说:你关押我这么久,我今天才识破你,今后再也不会消极承受你的关押迫害了。不怕死你就关押我,我就这样天天发正念解体你,直到把你彻底解体掉!此后我天天运用功能,摧毁旧势力对我安排的这套关押迫害系统,天天正念清理关押和迫害我的一切邪恶生命,包括一草一木背后以及空气微粒中的邪恶因素。几天的功夫,我感应到院子里的小草都想跟我说话,都希望我快点回家。接下来,劳教所大队长主动向所长请示,决定带我去监外医院“就诊”,我知道是师父要救我出去了。车子一出劳教所大门,我眼前豁然一亮,立刻心生强大的一念:邪恶的劳教所,你再也关不住我了!永远关不住我了!
医院里,大夫给我做胃镜,镜管儿在我食道里反复插下去再拽上来,恶心痛苦的我直流泪,真是生不如死的感觉啊。我闪出的第一念竟是“快点让我死了吧,我实在受不了啦”!他们一边不停的拽,一边看着电脑彩屏说没事儿。我痛苦到极点了,突然间,我想起我是要回家的,怎么能承认“死”呢?于是来自我生命深处每个细胞乃至生命的本源,发出凄切的呼喊:“师——父——救——我!”尽管是在心里喊的,可那声音仿佛响彻了山谷和云霄,响彻了层层天体和宇宙,久久回荡不息……一霎时,医生惊呼:快来看哪!看这指数都到哪儿了!医生面面相觑,乱作一团。我却感动的流下泪水,因为我心里清楚是师父来救我了——我隐约听到自己呼唤师父的声音依然回荡在耳边。
回到劳教所,队长和狱医都劝我吃药,劝我做手术。说我只是胃里长了息肉,只需要做个小手术,把息肉切除就好了。一会儿又说不做手术有危险。我知道她们所谓“胃里长了息肉”的说法是避重就轻了,师父演化的一定是生命垂危的状态。我明白自己根本没有病,多危险的状态和表现都是假相,都是师父为救我出狱而演化的。我坚决抗议做手术。
我告诉家人,只有向劳教所要人才是真正的帮我,最终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然后我分别给劳教所长和队长写了劝善信,要求无条件释放我。信被交上去十天后,我被通知“打行李”……
我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神迹的展现。比如在粘贴大法真相“福”字时,我担心贴倒了,心想:要是来点光就好了。结果随着一念的发出,每揭开一张真相粘贴,就会双手放红光;一天晚上,我去粘贴真相资料,刚把资料贴在电线杆上,后面有人径直朝我走过来。我就在心里劝他“快回去”,他果然立即掉头往回走;有一次我在白天发资料,胡同对面过来一位怀抱小孩儿的长者,显然已经看到我了。我默默的打过去一念:我在救人,请你先到别处去吧。长者真就哼着小曲儿往回走,出了胡同口,拐弯去别处了;有时发放真相资料,会遇到住户家的狗狂叫,我就想着从另外空间拿来一块布,把狗嘴捂住。结果那狗真象被人捂住嘴似的,哼唧两声就被什么噎回去了;经常在坐火车的时候,我对同一车厢的人动善念:想听大法真相的主动过来吧。不一会儿,就会有人主动坐到我旁边,主动与我搭话,也便有了愿意“三退”的人……
无论人类自以为如何,人类的科学在佛法面前也不过是小儿科而已。或许发生在大法弟子身上很平常的事情,却是人类科学几千年都无法达到的——这正是宇宙正法时期觉者下走在人间时给人类留下的神迹。或许人神同在的一页很快就要翻过去了,然而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一切,怎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它将永远载入正法的史册。万千的神迹和辉煌,将会万古流芳!
(明慧网“神在人间”征文选登)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html/articles/2011/3/10/123721.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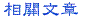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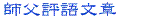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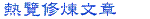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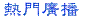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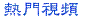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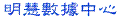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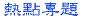
 迫害致死
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