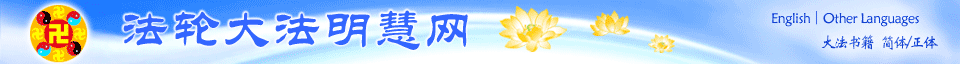【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七日】二零零二年八月份,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关进北京大兴劳教调遣处,恶警要求点名答“到”并低头。点到我的名字时,我既不答“到”,也不低头,恶警就对我拳打脚踢,拽着我的头发往下拉,强行让我低头,然后拽着我的头发把我拖进了调遣处的大门,要我蹲着,我不蹲,就站着。
中午吃饭时,我也不吃,因为打饭时要说“我是劳教人员某某某,我请求打饭”,打过饭之后,还要说“谢谢!某某队长”。我不是劳教人员,我也没有违法,我宁可不吃这饭。后来值班的送来一碗菜汤和一个馒头,当时天气非常热,我一下子把菜汤喝完了,才发现碗底全是沙。大兴这个地方就是个沙地,劳教人员的菜一般都没有洗干净,不管是什么菜,里面都有沙,很碜口。
吃完饭12点,警察要刚来的都蹲着,却叫我去“飞”着,我说我不懂,我不“飞”,她就叫几个普犯过来,让她们强迫我“飞”,就是:双脚站拢,腿站直,弯腰成九十度,头触墙,双手往后翻至贴墙。这种方式不打人,可是长期这样比挨打还难受,难熬。6月份的天气很热,我身上的汗直往下淌,地面打湿了一片,同时我的鼻孔里也在往下滴青色的水,那是我刚喝下去的菜汤。我在看守所绝食27天,被灌食时插进去的管子早已把鼻孔到胃部的通道打通,所以我身体下弯时,胃部的菜汤就顺着通道流出来了。这样我“飞”了两个小时,到警察上班时就叫我到她的办公室去。
几个普犯跟我一起来到警察的办公室,拿出纸和笔,要我写不炼功的保证,我说我不写,她们说:不写也得写,这是这里的规矩。我说炼功没有错,也不违法,对人身体有好处。她们说:你甭跟我说这些,我听的多了,我们要的是保证,我们要交差。我还是不写,她们就打我,几个普犯围着打我,这个打一阵,那个打一阵,将我推过去,踢过来的,一个警察穿着皮凉鞋踢我,把我的左小腿前面踢破皮,流出血。
在打的过程中有人敲门,一个警察进来耳语说:“小声点,外面听的很清楚。”这样他们就把门窗关住,用报纸把窗户蒙住。又逼我写,我还是不写,她们就反扭着我的手,用钢笔在我的手臂上乱戳,笔尖戳进肉里,有的戳痕里墨水也浸入肉内,在我的左手臂上至今还有两个带墨水的伤痕。普犯们在纸上写上污蔑师父和大法的话,强行贴在我的身上,我不允许她们这样做,她们就把纸放在地上,几个人拉我扯我去踩,我挣扎着,她们又把纸搓成团,强行塞进我的裤裆里。一个警察还是一个犯人(现在记不清)猛抓、抠我的左胸,把我的胸部抓破。她们把笔塞到我手里,把我的手握住,捉着我的手写,我奋力反抗,结果在纸上画出一堆乱字。因为看不清楚字,她们交不了差,就继续逼我写, 我不写,她们又让我“飞”着,同时把我的双手往上提,把我的头往下按,在这两股反向力的作用下,使我疼痛难忍,发出叫声,我越疼,她们越使劲,我想她们整人的办法真多真毒啊!
中间还经历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当时也被她们打蒙了。还记得她们又问我写不写,我说不写,一个普犯就左右开弓的打我的耳光,左手打我的右脸,右手打我的左脸,抽来抽去,不断的抽,她每抽一下,我就说一声“不写”,也不知被抽了多少下。然后几个普犯就捉着我的手强行在一张纸上歪歪扭扭的写了所谓的保证。我不承认这是我写的,我被她们折磨的精疲力竭。因为衣服已被她们扯破,她们就找了一件衣服让我穿上出了警察的办公室。估计可能是晚上八、九点钟吧。出来之后,普犯们又带我到劳教人员那儿去学习规章纪律,没站一会儿我就晕倒了。晚上警察还特地安排一个人看着我,怕我出什么问题,那个看守的人问:“你这身上都是她们打的吗?”我身上都被她们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
北京大兴调遣处繁重的奴役劳动,是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除短暂快速的吃饭、如厕、洗漱外全是在奴役劳动,即使这样还不容易完成繁重的定额,每人每天要包六、七千双筷子,甚至上万双筷子,就是餐馆饭店用的那种一次性的卫生筷子。劳动时不准讲话,不准交谈。没有完成任务就加班。
生活环境很恶劣,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住二十多人,床上睡不下就睡地上,头在这张床的下面,脚在那张床的下面,身子在过道里,没有电扇,大家还都在屋子里的桶里大小便,因为门被锁着,屋里充满的汗气、闷气、臭气、臊气可以把人窒息。我几次被这种气味熏的受不了了,感到快要窒息了。这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白天是劳役场地,我们吃的菜里,喝的水里有很多沙,就象是用的是黄河的水,每天出很多的汗,却不让洗澡,只是用点水擦擦,我在那里的二十多天里只洗过一次澡,那就是离开那里的头天晚上。中途洗过一次衣服,衣服是这样洗的:因为没有衣服换,大家只脱下外衣,穿着胸罩裤头继续干活,让一个人把大家的衣服都拿去洗,洗完就湿的穿上,让它在身上自然干,然后别人再把这个人的衣服拿去洗。
严酷的奴化管理,把人训练成奴隶。那些东西我不想再去想,再去讲了,在中共的看守所、劳教所,人格、尊严被践踏,在那种奴化制度下就更没有了人格尊严可言,有的只是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