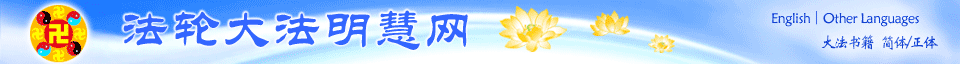【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五日】我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非法判刑七年,关在浙江省女子监狱。我想谈一谈在这七年的迫害中是怎样走过来的,其实念一正,就会显奇迹。
我娘家是浙江缙云,夫家是浙江玉环。九七年底随着先生带着两个幼小的儿子,从浙江玉环来到上海市松江区做饲料生意。九九年五月底经朋友介绍有幸得大法,得法不到两个月,电视里就出现铺天盖地的谎言,当时因为自己刚得法,对此谎言也不重视,整天自己忙于做生意。有一次,功友拿来好多封讲真相的信,寄给各个部门的,当时我看她怕心很重,带着白手套在操作。我就说:这有什么好怕的,讲明真相是好事情,人家乱发广告都没事,不用怕,我来帮你做好了。
从这天起,我基本每天抽时间,骑着摩托车到处寄发。有一天发好回来,大概晚上七点钟左右,儿子还在做作业,我到厨房倒开水,突然间看到窗外,师父站在半空中,面对着我,身穿黄色袈裟,单手立掌,面带笑容,左右两边还有一个圆的不停的在转,我立即跪下,连声叫:师父、师父……激动的泪流满面。师父笑眯眯的慢慢远去了。
从那天起,我坚定正念,真正走上了讲清真相、揭露谎言的行列。但没注重学法和发正念,因此也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把真相传单发送到浙江缙云(娘家),在二零零二年的一月份那边的同修被绑架了,她们没有守住心性,把我说出来了。缙云公安局、“六一零”连夜赶到上海,和松江“六一零”联合一大帮人来到我的住处,强行把我抬到车上,连夜把我绑架到缙云看守所,把我关進一个所谓的提审间里,一连四天五夜都不让我睡觉,我不承认他们的一切,也一直给他们讲真相。
警察把功友的口供给我看,我也全盘否定,到了第五天晚上下半夜,一个公安局、“六一零”的主任值班,重重的打了我一耳光,气急败坏的骂我不真、不善,自己做的事不敢承担,等于把责任推给功友。因我平时没有好好学法,所以法理也不清,觉的自己做过的事不承认是不对的,要敢作敢当,所以我就承认了。
这一承认,我的魔难也开始了。关進看守所的第一关就要背看守所的监规,什么“六不准,六做到”,我拒绝背。我说:我是大法弟子以真善忍为标准,不是以监规为标准,大法弟子绝不背监规。当时站在那里的大法弟子有十多个,看我不背,大家都不背了。指导员、所长气的脸都歪了,叫其他人都回监室,叫我跪在那里,一跪六个小时。从此,我不是被强迫跪就是面壁罚站。过了几天我们全体学员开始炼功,所里就用各种残酷的手段阻止我们,还让武警架着机枪守在我们边上,叫我们跪在那里,武警穿着皮鞋用力踢我们,我是被折磨的最惨的一个。天天戴着脚链、手铐,不能炼功,我就背《洪吟》。看我背法,指导员就把我手上的手铐和脚链锁在一起,人就不能站也不能走。后来我以绝食抗议。所长、指导员都说我:是你带的“好头”,我没去之前她们都很好,我一進去全都变了。住所检察院也来找我,说我这个样要给我判重刑。我在缙云看守所被折磨了七个月。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我被缙云法院非法判刑七年,送进浙江省女子监狱。一入监要面对的事情就多了:要报告、要学习行为规范、上政治课,还要点名签到,要给家人写平安信,等等。我一律拒绝不配合,监狱每天想尽办法折磨我。不管她们使出什么招术,我都用背法来对待。有一次中队长一定要我报告,我决不报,她气狠狠的叫我站在那里不准动。我站那里又开始背法,她和娄警察拿电警棍电我,刚电到我嘴巴,我马上大声的喊: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再电就电不出来了。周围的人见此景都发呆了。
她们费尽心思找各种借口来折磨我,一会说我不做作业、不看书、不听录音、政治不考试,还说我在会场上高声呼叫大法口号,干扰演讲,以种种借口,一会叫我站这站那,又把我拉去关禁闭,在严寒零下五-六度,我只穿了一身单薄的衣裤,一条两斤多重的棉被。包夹犯们说:警察说了,你要报告警察,才可以给你拿你的衣被,否则不可以。神奇的是我一点都不冷,再冷我也不可能报告。几个包夹犯穿的象熊猫,手脚还抱着热水袋,还说冻死了。这样三波四折都改变不了我。警察说:反正你不肯学习,就到工厂劳动去吧。开始就白天奴役劳动,后来说晚上也要去,我不肯去,包夹把我拖到工厂,坐在工厂里我也不劳动,后来警察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劳动。我说每天将近十一小时的奴役劳动时间,劳动法规定的时间早已超时了,晚上本来就不应该出工。从此以后,本中队的同修基本晚上不出工了。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中队里的阅览室,不是给服刑人员看书阅报的,是专门折磨大法弟子的场所。每位大法弟子只要关進去,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达不到监狱的目的别想睡觉。还要用各种方法摧残大法弟子。進了这个门没几个能幸免的,至今还是如此。在里面行凶的这帮人,都是经过监狱专门训练出来的。监狱每年要培养好几批这样的行凶者。因为每个中队都设有这样的场所。当时我知道此事后,去找中队的彭明菊指导员,我问她为什么把大法弟子关在阅览室里,每天都有打骂声,而且整晚都没得睡觉,剥夺睡觉权利,你们是在违法操作,知法犯法。我还告诉她迫害大法弟子后果的严重性。她再三辩解,我也再三相劝。过了不到一个月,监狱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规模越搞越大。监狱里的新大楼三楼,有十一个监室,总共可以住一百七十人左右,监狱把整个楼的人清空,专门用来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信仰的场所。比较坚定的大法弟子抽到这里强行“攻坚”迫害。监狱抽去四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一日,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日子。关進去的大法弟子都配备六名犯人,四名狱警。六名犯人叫:李雅珠、陈桂香、沈来、王明亚、马捷、陈柔然。四名狱警叫:余雪玲、黄英、黄金兰、李民。她们自己每天二十四小时倒班轮休。对我二十四小时轮流用各种残酷的手段摧残。每天放那些污蔑大法的电视,有几个犯人也侮骂大法与师父。犯人把写好的东西叫我抄,我不肯抄,她们就每天不给我睡觉。我一闭眼睛犯人就用风油精当眼药水,把我整个眼和脸都涂上。还每天几次给我灌了一些不明药物。沈来和马捷拉着我的双手,不停的转圈,转的我头昏脑胀,天昏地暗。特别是陈桂香力气非常大,她是大伙房的一把手,人高马大,监狱里力气最大的,这次把她抽调来就是做打手的。把我身上拧捏的黑一块,紫一块的,有时抓我头发,打我耳光,骂大法、骂师父骂的非常难听。我多次善心相劝,告诉她们不可以这样做,并且也说明迫害大法对她们将来的不利。陈桂香说:我不信也不怕。
大热天室门紧闭,没有一丝通风的地方,连上厕所、洗漱都不可以到卫生间去,室里虽然放着一只马桶,但整个室里,包括马桶的里外都贴满了诽谤师父与大法的标语,如果我要用马桶,随处都要碰到标语。我不用又憋不住,当时我真的要崩溃了。她们每天总会想出新招术来折磨我,我真的无法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达她们的所作所为。而且警察的言语也是比较恶劣的,警察余雪玲说:到了这一步你脑子还转不过弯,说明你肯定有精神病,国家已经统计过了,不肯放弃法轮功的都是有精神病的,再说你小时候得过脑膜炎,留下了后遗症,肯定有问题。警察李民说:你不要硬了,我们还没到最后一步,到时给你打一针,你什么都忘了。警察黄金兰说:我们知道你不会放弃法轮功,但我们只需要你表面做一下就可以了。监狱花如此大的精力,达不到要求,监狱是不会甘休的,你自己聪明点少吃苦头。其中还叫来已转化了的来做我工作,有的是博士后,有的是教授,叫来的同修被我讲后,都说自己后悔了。包夹说叫来的人反而被我给转化回去了。后来就没有叫同修来了。
后来陈柔然和马捷跟我说,监狱里已经叫李雅珠犯人打申请报告了,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每天给你打针吃药,跟一帮疯子关在一起,不是神经病也要叫你变成神经病,让你永远失去记忆。当时由于自己学法不深,再加上二十多天没睡觉,其实最关键是自己还有怕心,没有放下生死。听她们这么一说,内心马上起了怕心,正念就不足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白天黑夜也分不清了。过一会,又進来几个说:车来了,车来了,七医院(就是精神病院)的车在楼下等着,这些东西如果你不抄,马上就送你去了。我坐在那里糊里糊涂象个木头人,她们摁着我的手,抄写她们写好的东西,我眼睛也没看就抄好了。黄金兰警察说:马上给她睡觉。我这一睡好象睡死过去一样,但是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里看到一个用冰雕塑的人像,有些部位在融化,有些部位碎了。醒来后,知道这个梦是师父在点化我,因为我想修到一定程度,身体是透明的,那用冰雕塑的人就是透明的,已经碎了,融化了,肯定是不好的。由于怕心的作怪,念还是正不起来,看我睡醒了,几个包夹又在说了,真麻烦,监狱领导说了,光抄写不发言,医院还是要去的。自己的正念正不起来,在这无奈下,我又配合了。在三楼三十七天下来,同室的人见到我都哭了,说我变了个大样,老了十岁。在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头脑慢慢的清醒过来了,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损大法,但内心里还给自己找理由,我坚修大法始终没有变,在三楼的所有一切是她们逼的。师父应该会原谅我的。但包夹和警察也都这样劝我:修炼是修心,你心又没变,是我们逼你的,你师父要怪罪肯定也是怪我们。她们说的,我觉的也没错。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一位老乡同修塞给我一篇新经文《大法坚不可摧》,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特别醒目的几句,我不知看了多少遍。有一句是:“因此一些学员在被迫害的痛苦中承受不住干了作为大法弟子绝对不应该、也绝对不能干的事,这是对大法的侮辱。”还有一段是:“即使不是真心的也是在向邪恶妥协,这在人中也是不好的行为。神绝对不会干这种事。”还有两句是:“然而任何一个怕心本身就是你不能圆满的关,也是你向邪恶方向转化与背叛的因素。”我看明白后,懊悔万分,痛恨自己,连生死都放不下,算什么大法弟子,转念一想,悔恨已晚,跌倒要赶快爬起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天,我写好一式三份的声明书,监狱、大队、中队各一份,警察收到声明书非常的生气,黄金兰和余雪玲找我谈了很多,看我谈不通最后就说:你余刑还这么多年,以后的路你会很难走的。我说:为了维护真理,赴汤蹈火义不容辞。黄金兰说:看你是太糊涂了,关到阅览室清醒一下吧。就这样又把我关進阅览室。这次進去我正念很足,丝毫怕心也没有。我什么话都不讲,每天就是发正念,背《洪吟》,顺背倒背,脑子里非常清净。这种状态过了十多天的时候,我的前额和头顶有微微的震动感,开始我还不在意,后来就越来越明显。我想这次做对了,师父在鼓励我,我要更加精進。在二十天左右监狱里吊死一个人,监狱乱了,人心惶惶。警察也没心来管我,关了两个月就把我放出来了。
这次出来我完全改变自己,到工厂我也拒绝奴役劳动,整天闭着眼睛学法发正念。凌晨四点钟起来炼功,监狱为了阻止我学法炼功,想尽一切办法折磨我,一次又一次的关禁闭,戴手铐,用捆绑带把我手脚身上捆起来,但是我念很正。我跟警察说:不用捆了,你再捆绑我都要炼。警察说:这是什么地方,还给你炼功。我说:修炼是不分环境的。她们三个警察摁住我,把我绑的严严实实的,绑好走开不到五分钟,总有一只手自动会松开,我马上把全身的带解光,又继续炼。她们大年初一没来绑,初二到初四连绑三天都是如此,她们就没有信心来绑了。
这次禁闭室关了五十七天,看我每天学法炼功,这么清净,警察又把我拉回中队,把我一个人关在一间,与外界隔绝。白天晚上各派两名包夹看着我,我炼功就把我拉住,把警察叫来给我戴上手铐,我就大声的洪法,讲真相。她们最怕的就是大声宣扬,她们都拿我没办法。我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智,也真正让我领悟到师父讲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还有就是一定要静心的多背法,师父也讲过:“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扰〉)
有一次,一个大队长陈X找我谈话,说现在有新法律出台,象我这种行为要加刑。我说:我的一切不是你们说了算,一切由师父安排。陈X还说我是个冷血动物,不要亲人,监狱里只有我一个独类的,不打电话、不写信、不接见。不是我不要亲人,是因为这些待遇都是有交换条件的。我决不做违背原则的事。这几年为了阻止我修炼,一会把我关到禁闭室,一会关到阅览室,一会关到医务室。关来关去,因此包夹犯也换了几十个。她们开始不理解大法,最终都明白了真相,认可大法好,有的说出去一定炼,有几个在里面就得了法。《论语》都背的很流利。她们明白了大法,了解了真相,生命也因此而得救,我为她们高兴。
但也有不幸的事,在三楼时那个叫陈桂香的犯人,当时骂大法骂师父骂的这么凶,打我也打的这么狠,从三楼下来以后,子宫一直出血,后来查出得了子宫癌晚期,当时就保外了。还有监狱长蒋雷(音)(现在监狱长方清红的职位,以前就是她做的),她也得了乳房癌。其实我也向所有来做过我工作的狱警讲真相,可惜她们听不進去,在三楼参与迫害我的四位警察,后来有三位都调开了迫害大法弟子这个岗位。唯有余雪玲警察,从大法弟子被关進省女监开始干,积极的干到现在,从中队长升到教育科副科长,她身体很不好,毛病很多,可惜她就是不悟。我曾经也多次相劝,叫她考虑后果,为自己将来负责。她总听不進去,跟副监长方清红一拍一合,用心邪恶,对待法轮功学员非常残忍。
离出监还有两个月,监狱又把我关到禁闭室,关進去十天,我全身麻木,不能动,警察叫包夹把我背到医务室,医生查了查什么话也没说,包夹说我血压太高造成的。好心的包夹哭了,说我就要出监了,还变成这个样,出监那天难道还要叫家人用单架抬出去吗?但我心里明白,师父讲过,大法弟子身上发生任何事情都是好事。看我这个样,监狱第二天派车送我到杭州同德医院去检查,查了老半天也查不出什么结果,当天就回到了监狱的医务室,任何药物都没用,第二天好了,手脚都会动了。监狱原本把我关在禁闭室到出监,没有想到突然发生这个事,看我好了,监狱也不敢再把我关到禁闭室了,就把我转移到阅览室,关到出监,所以发生此事也不是偶然的。
在这一次次的肉体摧残、高度的精神折磨,七年到了,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我走出监狱大门,三个男人齐齐的站在那里,两个儿子都长这么高了,变了很多,我都认不出来了,当时大儿子才十一岁,小儿子才七岁。当时我被绑架的过程中,两个小孩被吓的到现在还有恐惧感,丈夫那憔悴的样子老了许多,但最疼爱我的母亲带着伤心与不满,零七年离开了人间。伤心的是女儿最后一面也见不到,不满的是,女儿修真善忍也要坐牢。
中共政府这荒唐无理的打压,残害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多少个孩子成孤儿,多少个父母因此伤心过度提早离开了人间。本来家庭经济比较不错的,因此成了欠高利贷,我和丈夫一同在上海做饲料生意,本来做的很不错,因我被绑架后,丈夫精神颓废,无心经营生意,该收的款收不進,不该亏的亏了。我七年回来欠亲朋好友的不算,高利贷欠了几十万。为了还高利贷只好把老家的房子卖掉,因为上海的房子房产证没办好不能卖,把婆婆安排到敬老院,因此也要受中共的刁难。
无辜的被折磨了七年,没想到出监了还要受中共无理的刁难。因我坚修大法,九十三岁的婆婆村里的敬老院都住不進去,政府要我说句不炼法轮功了,否则敬老院不收。还有,我小儿子户籍在台湾,也因我坚修大法,说我儿子住在大陆是黑户违法的,到时遣送回台,五年不得入境。当地政府还给我丈夫说:只要我说句不炼了,什么事都好办。我跟丈夫说:不用担心,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现在我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高利贷还清了,婆婆的事虽然用钱大一点,但也安排妥当了。我相信只要信师信法,一切都在美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