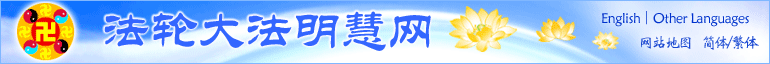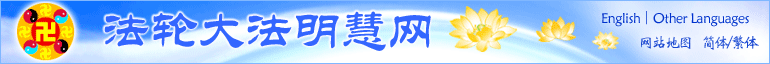|
【明慧网2004年6月26日】我是1995年12月开始修炼大法的。修炼后,我在大法中不断的净化自己的心灵,身心都发生了改变。1999年7月,以江××为首的邪恶之徒开始陆续的在北京,天津,辽宁,山东,湖北、湖南等各省、市抓捕法轮功辅导站站长,和他们认为的大法学员中的“骨干”。大法学员陆续進京上访,要求无条件释放被关押的大法学员,不断的上访,不断的被抓,被打,被拘留,被劳教,被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
上访是国家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了向国家反映真实情况,为了不让大法学员再继续被非法关押和迫害,我于1999年9月初和10月初先后两次進京上访。两次都是还没到信访办,在所住地就被当地派出所民警绑架,被吉林住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送回当地办的学习班拘留了15天。当时的文件表明,要两次拘留才可以办理劳动教养手续,吉林市610为了不让大法学员继续進京,就采取了办学习班和拘留循环式手段,只要够两次就可以送去劳动教养。在第二次被拘留时,大法学员集体绝食,要求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大法学员。 2000年11月21日晚6点左右,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吃晚饭,突然来一帮人说有急事找我丈夫王建国,说是市局下的令,把我公公、婆婆、丈夫全部绑架走后,拿出搜查证放在桌上要非法抄家,里里外外,就连地窖也搜。他们在我屋里找到两张硬盘、还有动画片、歌曲、游戏等各种光盘,共有十多个,还有丈夫的BP机等物品全部被非法抄走。我在1999年9月進京上访时,有一个和这次一样的摩托罗拉BP机,被昌邑区哈达湾派出所民警抢走。 2001年11月9日我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于11月10日下午2点左右在天安门金水桥处打开横幅“还法轮大法清白”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让世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让江氏集团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我正喊着,两名便衣警察直向我扑来,他们把我强制拉上警车,并把横幅撕成两半,我依然紧抓着横幅。上车后我发现车上有一位老太太,也是大法学员,正在告诉另一恶警:“你所做的一切都要自己去偿还,希望你不要再做错事,放了大法学员。”正说着,我被抓了上来,她一见到我,就对恶警说:“放了她。”我听到后也说:“放了她……”没等我说完,恶警就踢我的肚子,不停的打我,我就继续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不停的喊,恶警就把我按到车座下,用腿用力压住我的后背,不让我起身。直到天安门派出所又出来两名恶警,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后,我站起来吐了一口血,包在卫生纸里,我正告他们说:“这是你们的‘杰作’。”其中有个恶警说:“你把它放好当证据。”我说:“那是自然,我一定留着。”随手把它放好,这时我看见打我的那个恶警脸色发青,被吓的够呛。 没过几分钟,他们要给我照像,我不配合,又是一顿拳打脚踢,他们还用一个黑色的东西打我的腿,打的麻麻的痛。照完像他们开始翻包,我的包内有两个充电器被抢走,还有证件、手机、钱包、磁卡、《转法轮》和经文。他们把我的磁卡拿出来边玩边往和我一起被绑架来的大法学员头上扔。我正告他们不要动我的东西。 因为他们知道了我的地址,所以给驻京办事处打了个电话,让来人接我。随后把我关進铁笼子内,里面有许多大法学员,都是来打横幅被抓没报姓名的,她们看我被打的够呛,有的去质问恶警、有的扶我坐下。我坐下想了会儿说:“我应该把书要回来。”旁边有一位男同修说:“你一定能要回来的。”我站在铁笼子门口,对打我的恶警大声说了三遍:“你必须把书还给我。”“书是我的命,否则我就死在这里。”那个恶警听后把书拿过来只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要别一本(经文),他说:“等你走时,一定再给你另一本,先给你一本看。”我拿着书和大家一起学起法来。 大约6点左右驻京办事处的人来接我,姓石,还有好几个,我拿着书出了铁笼子,心想:出了门我一定要走出那个大门。到了门口,打我的那个恶警把我的包还给我说:“她不老实,得给她戴手铐”。我一听就说:“我又没犯罪,也没犯法,凭什么给我戴手铐子,我不戴。”说完我转身刚要走,这些恶警一拥而上,抓手的抓手,抓脚的抓脚,要给我戴手铐,我边挣扎边喊:“师父加持弟子……”我喊完刚闭嘴,就感到嘴里好象有什么东西,是恶警们把电棍放到我嘴里不让我喊,怕他们的恶行曝光,想用此来堵我的嘴,我用力咬住,另一个恶警用力一脚踢到我的阴部,只因踢得太狠,把我踢得一下头撞到墙上,晕死过去,不省人事。 后来,一位目睹了这一幕的福建同修告诉我,我昏死过去后,恶警们给我打了一针,有一个恶警看我晕死过去,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旁边的姓石的一看害怕了,怕把我打死不好交差,马上把他拉住说:“再打就打死了。”这样恶警才住了手,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把我抬上车拉到办事处。 我被拉到驻京办事处,晕死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在驻京办事处时,我对姓石的多次提到我要回家的事,他却说:“我给吉林打了好几个电话,他们说已经派人来了,叫我等着,我也没有办法。”我说:“我不用他们来接我,我自己能回家。”他把我一个人锁在住京办事处8楼的一个房子里,不让我出去,怕我跑了。我当时的身体根本就动不了,整个头全是包,大包上有小包,包上还有包,右眼被打的象冒出来一样,颜色是紫黑色,嘴角被打的直流血,两个手臂被撅的动不了,左边的大腿从臀到膝盖整个被打成紫黑色,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遍体鳞伤,体无完肤。怎么可能跑得了呢? 我知道他们把我放在这里时间越长,我身上的伤就在慢慢的有所好转,所以他们就往后拖延时间,越晚来接我说明他们就越见不得光,怕我被打的事传出去。我在这里住了两天,他们才把我接回吉林。接到当地时,市公安局和船营区沙河子派出所和昌邑区哈达湾派出所等恶警一起研究怎么办,只因在我回来前他们曾向我家人勒索钱财,遭到拒绝。所以等我回来时他们看我伤的很重,不知怎么办好,在一起研究了很久,最后决定把我推给昌邑区哈达湾派出所。他们骗我,说是要送我回家,结果把我拉到昌邑区虹园村玉湘园汽车旅店的二楼,严格看管起来。 昌邑区哈达湾派出所恶警蔡金主管此事,整个二楼都被包了下来,这一切早都已经安排好了,虹园经济开发区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也在我坐的车上,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他是谁,后来我看到这个人有一些不正常,不是看着我,就是和我谈完话后,不断思索好长时间,然后还是问同样的问题,给我的感觉是这个人好象是在做记录。我当时还不住的说他,是在往脑里记些什么,可是他就是不出声,还是不断的用大脑在作记录,我在这家旅店里给他们讲了一夜的真象,并且不断的提起我要回家的事情,可是蔡金就是不让我回家,更别想见到我的家人了。 第二天一大早蔡金就跑到市局,把市局负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和他的秘书一起叫过来了。蔡金说他是局里来的,专门为我这事来的。这时那人问我怎么回事,我问他说:“你没说话呢,为什么就开始给我记笔录?在记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问他为什么不谈我在北京被打一事,他却不敢面对此事,最后看我追的比较紧了,说:“一会儿单写。”表现很不满的样子,非常生气,因为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所以他们很不愿意提这事。因为他们的目地就是要把我送到劳教所去。到最后他还想骗我不提在北京被打一事,找借口说一些别的事,当时我就说要写这事,他就不让写了,说:“写两句就行,用不着写那么多。”我正告他们:“必须一字不落的把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写下来,否则你们刚才写的一切我都不承认。”他们没办法只好把我所说的全部写了下来。 最后和我说要送我到劳教所,我对他们说:“我被他们打成这样,你们不送我回家,还要送我到劳教所,你们有没有人性?我说什么都不会去的,我死也不去。”说着我就要起身,蔡金一把把我按到床,抓住我的手就不放,后来我就晕死了过去。蔡金叫他们把我抬上床,过了一会儿,我醒了过来,他开车拉我到对面的饭店。蔡金拉我去吃饭时,正好我的家人到关我的地方来看我,这一切都是他们安排好了的,不让我和家人见面,就没有机会回家,当我回来时家人已经让他们给骗走了。我刚進门,就看见一个人好象是昌邑区分局的,他和蔡金不知说了些什么,就大声说:“我听北京的警察说给她检查过身体,什么事情也没有。”他们不知又在外面说了些什么,医生一進门什么也没说,就填了张诊疗小票给了蔡金。蔡金拿着这张小票就往楼下跑,我身边的人就说:“上对面的楼去做透视。”当我刚走到做透视室的门口时,就看见蔡金和一个医生从走廊的里边出来,边走边说着什么,把手里拿着医生给他的小票给了身边的这个医生。他接过小票看了看,走進透视室按动机器。过了一会儿,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蔡金拿透视的结果又快速的跑到门诊找医生签了一个字。这时我刚走到车前,我身边的人就说:“一切正常,按正常处理。”我说:“我要回家。”昌邑区分局的人一把抓住我,使劲往车里一推,还说:“進去吧你。”随后把车门一关,让蔡金开车到第三看守所。 他们让我下车,我说什么也不下车,他们四个人强行把我拽下车,把我抬進第三看守所里,我不断的挣扎,不断的大喊:“放了我!”没人理,后来蔡金一把抓住我的手,把我扣在了看守所门口的铁扣上。我在第三看守所里被非法关押了一个多月。 在这里有一个大法学员,也是从北京送回来的,被打的不断吐血,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去。看守所的大夫天天看着她,过了两天大夫看不行了,就打电话给派出所。第二天上午来人接到医院,吉林市各大医院都走遍了,打了一个点滴,和家人见了一面,最后还是被送了回来。回来的当天还很好,还说要和我一起走出看守所。可是第二天她又开始吐血,一连吐了好几天。我们这里有一个刑事犯人,家里祖传的中医大夫,把脉特别的准,看守所的大夫都不如她。就在这天晚上,这位大法学员要上厕所,我扶她去的,可是当她回来时我就感觉不对,她脸色发紫,混身抽搐,脉搏微弱,手脚冰凉,我立刻找来值夜班的管教,他也没办法,只好找来所长,所长让那个刑事犯人给这位大法学员把脉,最后的结果是,每个人都有三根主脉,而她只有一根了。刑事犯说:“已经没救了。”所长一听吓坏了,马上打电话找到负责人,他们把这位同修用单架抬到车上,送到二二二医院打了一针又给送了回来,这回看她还不如刚开始了,比刚才更严重。我就问他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没事,一会儿家人来接她就好了,现在就等着局长的批条下来,等着放人呢。我们一直等到晚上12点钟,局长的批条才下来,她的家人把她带回了家。 2001年12月20日星期四上午9时,我被吉林市昌邑区哈达湾派出所恶警蔡金、白某、乡里的一妇女主任,强行送入黑嘴子劳教所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二年。他们让我签名,无论他们说什么我都没有签;直到到了长春黑嘴子劳教所,我还是没有签。他们很失望的走了,我在劳教所里苦苦的度过了二年零二十天,这度日如年的日子,有谁能够想到在一个外表华丽的劳教所里,时刻都在发生着见不得人的恐怖的事情。 劳教所内阴风吹过,我感到无比寒冷,她们把我带到了看守班,分配到一大队,我被带到五楼。满屋的恶警看到我后,七嘴八舌说个不停对我大吼大叫,让我把身上带的书交出来,我不交。管教室内所有的恶警一拥而上,把我打倒在地,一顿拳打脚踢,还叫外面的护廊(非法轮功学员)打我,强抢我身上的书,棉外衣被撕坏,里面的小棉背心也被撕坏。恶警严丽峰说:“不把棉衣还她,把它扔了,冻死她,实在不行就让她尝尝劳教所内的28种刑具的滋味。”她又叫人拿出四、五个电棍,说:“把电棍都充足了电,让她尝尝滋味。”我的心更加坚定,我选择的路绝对没错。 2002年3月5日,长春市大法学员在播放新闻联播期间插播大法真象片长达三四十分钟,在国际上都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这事发生之后,邪恶之徒们开始又一次疯狂迫害,坚持修炼的大法学员一天24小时在寝室内被洗脑,不让睡觉。第二天恶警苏桂英上寝室找大法学员贾桂华,并打贾桂华几个大嘴巴。贾桂华对苏桂英说:“你所做的一切,你都要加倍的偿还。”苏桂英吓的退后几步,转身走出寝室。 当天各小队开会,目地是叫大家表明心态是站在法轮功一面,还是站在国家(江氏集团)一面,背叛国家要枪毙的,每个人都得说。轮到我时,我说:“我永远不会和法轮功决裂,一修到底。”恶警苏桂英大叫:“你站起来,出来!”我走到她面前,看着她,心里什么也没有想,我明白谁也动不了我,无论用什么方式都无法动摇我这颗坚如磐石的心。轮到了吉林市大法学员郑微,她说:“我以前所说、所写的一切对大法不利的一律作废,从此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学员。”会开到这,再也开不下去了,苏桂英立刻离场,告诉护廊和帮教下午再开。 到了下午恶警苏把郑微的档案拿来,当众让帮教读郑微的五书,以此威胁郑微收回上午的话,郑微并未收回。从那天开始,迫害力度开始加大,晚上9:00-12:00学习,不让睡觉,不到一周,又开始有新迫害计划,每天放恶人王志刚污蔑大法的录像、光盘,还强迫大家买王志刚诽谤大法的书。恶警们为了达到其邪恶目地,开始对大法学员進行突击式洗脑。一个人在寝室,四五个帮教放诽谤大法的录音,一天、两天……直到写五书为止。我当时想我不可能写,得想办法离开才行,大队学委刘亚茹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从今后你就归我管了,看你还写不写五书。”我想:“写五书,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劳教所成立文艺队时,把我选上了,我拿行李时,看见薛亚彬伪善的笑着对我说:“对不起你。”我很吃惊:“为什么对不起我?”她说:“没能在你走之前帮你转化。”我心想:“你太邪恶了,我要走了,你都不放过我。可喜的是我有师父,谁也动不了我,也转化不了我。这里太邪恶,师父不让你们继续迫害我,一切我师父说了算。”想到这,我说:“我现在很好,我以后会更好。” 到了五大队,2002年5月13日是师父的生日,就在这天,我和李红岩在窗外挂了一张写有“真、善、忍”的纸条幅,挂了一白天。敏感日期,她们在院内院外都有巡逻的,第一次他们没看明白是哪个窗户,等看明白时,我已经把条幅取下来了。她们发现后,把我叫到管教室问话,刚开始我没承认,后来,怕牵扯别人,就承认了。恶警李文娜也怕这事让人知道会影响一大片,就不了了之了。 2002年8月,恶警肖爱秋听恶人李淑兰(五大队帮教)说我给学员周永平经文(那时我不认识周永平),就叫我到管教室寝室,床上放着电棍,肖爱秋背对着我说:“这段时间你给谁什么东西没有?”我听后很吃惊,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她说着抓起电棍就电,我就躲,后一想,不对,就一把抓住电棍,正视着肖爱秋,对她说:“你要不就电死我。”肖爱秋害怕了,不敢电了。 文艺队有一个大法学员叫孙萌,2002年3月被强行送入劳教所,她刚到时就整天被恶警们用尽各种办法洗脑,她依然坚持修炼。在迫害加剧时,恶警对她一天18个小时不停的帮教,一个人不行,两个人。最多时,人数达到10多个人,在一个寝室内坐满了人,一人一句,还是没能达到邪恶目地。在这里也有许多坚持修炼的大法学员和亲人见面都是强行的,恶警们企图利用大法学员不修炼的家人的情达到其强迫大法学员放弃修炼的邪恶目地,但都没有得逞。 2003年2月份过年前期,阴历27、28在五大队各小队都出现了“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在文艺队也出现了,她们猜是我挂的,因为我在文艺队寝室挂过“真善忍”,还因此给我加过期,所以认定是我挂的。 新年刚过,一天,肖爱秋一大早就把我叫到办公室以我不写思想汇报为由,私自动用刑具,对我大打出手,两把电棍(一大伏、一小伏)一把手铐、三个皮带、五个管教、三个大队长:李文娜、王立梅、温影,二个管教:肖爱秋、张立红。他们从上午9点一直折磨我到下午2点多,才让我回车间,我的右眼和下额、脖子都被电伤,左臂被肖爱秋踢伤,两手和手腕被肖爱秋电的青紫而红肿,脸被肖爱秋打伤,右臂被王立梅踢伤,动不了,打的我遍体鳞伤。她们怕我出现生命危险,特派大队学委护夜,派非法轮功学员,一天24小时包夹。 2003年7月我从头到脚哪都痛,到医院检查,陈丽只给我开了止痛药,出了门我就晕倒在地。她们抬我做心电图,检查出心脏病,强行给我打点滴。我不打,陈丽恐吓我:“你要是不打就把你绑在床上强行注射。”我身边的张淑红、刘晶华按住我双手和腿,因当时浑身抽搐,无法自制,陈丽强行给我打了点滴,还对张淑红说:“不能让她动,按住她。”陈丽对所有不写保证书的大法学员都这样。 我第一次晕倒在地是2002年6月份,晕倒近1个小时没醒,肖爱秋一看吓坏了,马上打电话找大夫,李文娜小声对大夫说:“这个是没决裂的大法学员。”医生一听,气坏了,大喊大叫,叫我起来,使劲扒我的眼睛,按我的人中,另一个拿个大针吸药给我注射(这是我醒后大法学员在旁看到告诉我的)。 在这个人间地狱里,这些事情时常发生,到现在这里还在继续发生着血淋淋的迫害事实。这些事就在您的身边发生着,大法学员为了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而遭受邪恶之徒的恶毒迫害。请大家认清对大法学员迫害的本质,不要再听信江氏一伙的欺世谎言了。 请记住:不管什么样的迫害,我们大法学员不会放弃修炼,因为“法轮大法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