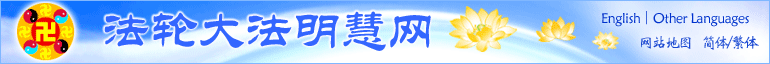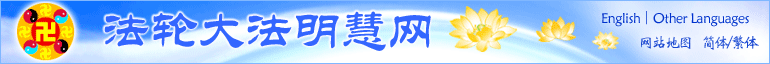|
【明慧网2004年4月18日】有幸倾听师父《在美术创作研究会上讲法》,懂得了作为一个美术创作的大法弟子在正法时期的角色与责任。师父说:“美术对于人类来讲是很重要的,它和人类其它文化一样,是能够在人类社会起到一种对人的观念上的导向作用,影响着人类的审美观念。”
记得第一次看到毕加索、梵高的画,本能的反应是不喜欢,不想看。但又知道他们是现代艺术史上最有名望的艺术家。有一位当代有名的建筑师开导我:“你现在不喜欢,是因为你还看不懂。”我为了看懂与理解他们,读和研究了关于印象派、后期印象派、象征主义、立体主义等等一系列介绍现代各流派的理论文章和书籍。我努力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画以及他们表达的是什么?我试着用他们的思路与眼光去观察与思考,我变得越来越喜欢他们的作品。从这一小小的经验中,可以看到我的本能的审美观是怎样在后天的教育及社会的思潮中演变的;同时真正的自我又是怎样被后天的观念掩盖了。 什么是美?什么是真正的艺术? 我从小就梦幻式地寻求“永恒与完美”,当我选择绘画作为自己的艺术生涯的时候,也是因为绘画可以表达“永恒与完美”。然而,海外学习和生活的负重,打碎了我想寻求完美与永恒的梦。失望使我以为世界上没有完美,也没有永恒,有的只是“破碎”。我把“破碎”当作人生唯一的真实;把美的定义局限在是“破碎”组合构成的冲突与对比中;也把表现“破碎”作为艺术创作的唯一真诚。我试着表现破碎与由破碎而引起的情感,也尝试各种现代派的手法来表达内心的感受。现代的审美观念又误导我,使我以为:“艺术史是直线上升与发展的,现代艺术对于传统艺术是一种进步,在今天这个后现代的历史时期,对于古典的美只是一种历史的审美情趣。现在还表达古典的美,只能是对现实的粉饰,是矫柔做作。” 1996年,当我刚刚得法的时候,就碰到一个障碍。那是读到《转法轮(卷二)》,师父对印象派和抽象派的论述。我不由自主的反应就是想和师父说:印象派和抽象派是不一样的,印象派是在室外写生,捕捉太阳下的色彩关系,是写实的。我感到自己什么地方不对劲,一个同修对我说:你肯定是错了,因为师父说的一切都是对的,是一个理,而不是对一个名词的解释。我当时也想:师父说的一定是对的,只是我自己还不能理解。第二年,有一个同修问我:你在看《转法轮(卷二)》时对师父论述的印象派这一段怎么理解?我说:跳过去。因为我还是不能理解,所以每当我读到印象派这一段时,就真的跳过去。自那以后,我画画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块小小的景色,那是非常美丽的天空与云彩,这块景色一天比一天大。有一天,我在为单位设计鬼节的路灯,我用铅笔单线画出了一个巫婆的脸,我的脑子想,她的眼睛和嘴巴应该镂空,灯光可以从她的嘴巴和眼睛里射出来。瞬时,强烈的、激光似的光从她的眼睛和嘴巴里面唰唰的射出来。然后我又想,巫婆的脸应该是绿的,我设计稿上的巫婆马上就变成了绿色的脸,我带着惊讶与恐惧。在我设计骷髅头时,我用单线画出一个侧面,脑子想,后脑应该画的比较丰满,才能让它的脑子装进去。刚想完,一个彩色的完整的脑子出现在骷髅头脑子的部位,我从来没有画过脑子,也从来没有见过真实的脑子,但是它就这样真实的出现在那里,凹凸不平,在沟沟坎坎之间,有一条浅蓝色的光,在不断地窜。这件事让我悟到好多东西,其中有一点,那就是,我画的每一样东西,在另外空间都会变成真实的物体存在。我第一次对师父印象派的论述有了一点理解。尽管印象派是在室外写生,但是,他们的笔触和形体都是不严谨的。那么他们画了那么多松散的东西,在另外空间就有那么多不严谨的形体。这怎么能算是写实的呢?我虽然在这一点上有了一些认识,但是对印象派的色彩还是非常的推崇。因为我感到他们是在艺术史上的一种突破。 修炼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在不知不觉中变化着。一天,我在一个画廊里,一幅巨大的油画吸引了我。它的不协调的色彩与混乱的构图,让我感受到画家作画时的紊乱心情;我想起自己以前有过的焦虑和茫然,然而当时的我通过修炼已经从这种心情中解脱出来,感受着平静的美带给我的愉快。这使我再一次思考:什么是美的真实?什么是艺术的真实?什么又是生活的真实呢?我在平静的心态下表达一种愉快的情绪不也是一种真实吗?为什么我以前如此地狭隘,把“破碎”看成是唯一的真实;把古典的美,看成是对现实的粉饰呢?当我从狭隘中走出来,感到眼界豁然开朗,不再被现代的各种理论和流派所拘泥。我开始欣赏古典的美,而且想表达古典美。这时,我感到自己象一根细细的长丝,从心中抽出来,可以编织任何图画。 两年前,有机会在巴黎的卢浮宫临摹古典大师的作品。我深深的感到在这些作品中有着学无止境的源泉。我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非常准确的冷暖关系,表现的恰到好处,这说明印象派并不是艺术史上对色彩的冷暖关系的创新者,在古典大师的作品中色彩的冷暖关系早已存在。当我再走到巴黎的奥赛宫,这里主要收藏着印象派的作品,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些我曾经崇拜的大师的作品变得黯然无色,它的颗粒和笔戳都是粗糙的,那些冷暖对比是简单化的夸张。这让我又想起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对印象派的论述。这一次使我真正体会到印象派对于古典艺术而言不是进步而是一种倒退。师父的一句话我是通过了这么多的反反复复才真正理解了。 师父在《美术创作研究会上讲法》说:“对什么是美、什么是人类应有的正确的美的感受,这是和人类的道德基准息息相关的。如果人把不美的东西当作是美,那人类的道德已经完了。” 我重新审视自己以前的作品,现在看起来,有好些都可以再画下去。然而那时候就不愿意再深入地画下去,认为已经很好了。这除了现代观念的影响外,我个人体会还有一个原因:身体上的懒散引起的思维与行为上的懒散,使我失去了作精心刻画的耐心与能力。在大法的修炼中,在物质身体的精力回复中,在渐渐地去掉各种执著后内心达到静的层次,也是能力恢复的境界。从这一点引伸,艺术史犹如艺术家群体的生命,她后期的各种流派犹如一个老人在衰亡中四处投医的药方,然而并不能解救她死亡的命运。只有大法中修炼的艺术家在返本归真中恢复了他们的能力,艺术也就返回到她的鼎盛时期。这也是师父对我们的希望。 师父《在美术创作研究会上讲法》以后,我内心虽然知道应该尽快地投身于美展的创作,但两个月过去了我却一笔也没动。是什么东西在障碍我呢?我从师父的讲法中懂得“人类美术作品的创作中心应该是神。”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神,我画不出自己没有见到和感受到的东西。我反复地读师父的讲法。有一天,想起以前有过的经验,我所画的东西在另外空间都成了真实。那么我画什么对人最好呢?那毫无疑问就是师父;那么我又画什么在正法中最有效呢?也毫无疑问,那就是把罪恶之首投入“无生之门”。我正式开始投入了创作。然而新的障碍又来了,看到很多同修都在画师父,尤其是看到一个个大的头像,就联想到文化大革命时画主席像,当时我又正好看了“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部反映文革的影片。个人崇拜及个人崇拜所带来的后遗症不时的袭来,我想是旧势力放到我脑子里,让我去怀疑,真正的我不会这样想,但还是挥之不去,我知道根本问题还是对“神”的不理解。 我从小在中国大陆长大,满脑子装得是“无神论”,记得刚到美国时,好几个宗教来找我们,都被我们拒绝了。基督教的牧师对我们特别好,使我们在不好意思下只能每个星期去教堂,然而我们无法接受“神”这个概念,每次回家后,我和丈夫就认真讨论关于“神是否真实存在?”这样严肃的问题,我们无法找到答案,就打电话和牧师讨论。第二个星期牧师在布道时谈到耶稣的神迹。那时的我非但不相信,还觉得牧师有意要说服我们,心里产生更大的反弹。修炼大法以后,我虽然知道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但对“神”还是没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与感受。我看到的师父是穿着西装的人的形象,也就用人的观念去想师父。后来发生一系列的事,让我切身感受到师父的无所不在。举一个例子: 去年,某报纸举办“儿童绘画比赛”。我在波士顿地区协调这件事。我们请了同修的太太,一位不修炼的常人作负责联系的人。由于很多读者有顾虑,参加的孩子不多。这位联系人对我们法轮功修炼者有一种失望,她感到我们做事虎头蛇尾。这提醒了我,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讲清真相,我们必须有一个完满的结束。这样我们找了场地展览这些作品,邀请当地的知名人士与画家们组成评选组,找了赞助人给评选的专家劳务费,也找赞助人为孩子们买奖品,定下了颁奖的日期。我看事情有了眉目,就想赶着去画我的画。但是汽车轮胎没气了,打了气又瘪了,就换一个新的。回家拿了东西准备离开时,汽车却发动不起来,报警器乱叫,没办法打了AAA,他们也没有办法。 我想到很多具体的细小的事还没有做,这样来去匆匆的,到那一天或许就是这些小事,会使我们整个事情前功尽弃,我决定留下来,把这些细小的事做好。这一决定刚做,报警器就停下来了。我多么惊喜啊,知道师父就在我的身边,师父希望我把每一件事都做好。我留了下来,安静地去做每一件小事。精心设计了奖状。评出了10不同栏目的一等奖,6个二等奖,其余的作为鼓励奖。我们感到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参与本身就非常有意义,就是应该给予奖励。但当时我动了常人心,感到鼓励奖不好听,如果用三等奖来代替,孩子拿到学校去就比较体面。我做完奖状就到店里去印刷。当我去取的时候,他们竟然忘了帮我印,我就等他们当场印,但是他们的机器又坏了。我想大概我又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想起那个三等奖,我做的不符合“真”,和同修商量下来,用“特别奖”给予特别的贡献。这样才符合真实。我们连夜赶做,再找了一家店去印刷,直到清晨。下午就要颁奖了,好像还有很多事情还没做。我在Mall里买东西,正穿过一家服装店,我知道自己应该添新的衣服,不能在公众场合老穿那几套衣服,但是现在又是什么时候呢?我对自己说:不要执著!但是一眼扫过去,却发现一条自己喜欢的裙子,我知道这样的裙子一般很贵,我再对自己说:不要执著!平时我很难在商店里找到自己喜欢的衣服,所以还是不由自主地走了上去,一看,竟然打很大的折扣,我心中暗喜,就买了下来。但是那天天很冷,我正犹豫该不该穿,当我走进家门,热气乎乎地向我袭来,我先是一怔,今天房间里怎么这么热?但马上又明白过来,怕什么呢?那里有暖气啊!我穿戴整齐,赶去颁奖。一路还在担心,那些小朋友都会来吗?我打过去的电话大部份只是留了言,没有得到确切的答复。当我赶到那里,看到大部份小朋友和家长都已经来了,一些同修带着他们不修炼的家属正在帮忙。我除了惊讶只能感叹: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操心啊,我真的仅仅是舞台上的一个演员,做着我应该做的。那天,每个人都很愉快,我们的评选除了专家评,还让当天的参加者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有一份评选权,选出自己最喜欢的作品。 有一个男孩画的很好,他几年前就要求学法轮功,他的父母跟着他一起参加九天的洪法班,7.20以后他父母就不炼了。当我们的比赛公布以后,一些也画得很好的孩子都因为父母的顾虑而没能参加,但这孩子说:“汪老师,我一定参加。”这次颁奖仪式,他的父亲开刀不能送他来,他自己乘车来。没想到他得了大年龄组的两份第一名,他父亲后来特地给我打了电话。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师父给他的奖励啊!有一个六岁的女孩子,他的父亲修炼,母亲不很理解法轮功。女孩画了一条彩虹,三个仙女在天空中,旁边有一朵荷花。她的母亲当时想:哎,怎么加了一朵荷花,是不是受了她父亲的影响?她女儿得了小年龄组的创作一等奖,母亲万万没有想到这朵荷花给她女儿带来的福分。一位家长对我说:他看到有绘画比赛的征稿,正好是最后一天,就对他们说:“你们的女儿画的这么好,为什么不参加?”他们匆匆寄出了稿件。没想到这孩子在小年龄组也得了两个一等奖。我们乘机会说了真相,想必他们会把愉快的感受传给他们的亲戚和朋友们。 颁奖仪式结束后,我进了一家中餐馆吃自助餐。服务员送来了祝福果,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你将得到你所尊敬的人的奖励”,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实际上我们能做成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帮忙,如果没做好,那一定是自己的执著造成的。然而最使我感动的:是几天来感受到师父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身边,为我操心着大大小小的事。我虽然看不到另外的空间,但我是真切地感受到:每当我做好的时候,师父会鼓励我;每当我做错的时候,师父会提醒我;而且当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时,师父会原谅我,再给我机会。师父的慈悲,不仅仅是对我,而是对每一位弟子,师父对我们的珍惜远超过我们对自己的珍惜。师父的身体力行,使我不由自主地从内心发出一个声音:“我们的师父多么伟大啊!” 这时候,我才发现,来自心底的尊敬和文化大革命的盲目崇拜是多么不相同。外表看上去一样的东西,实质却有着天壤之别。贫乏的人间语言不足于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在表达中又吞吞吐吐,还怕世人会不理解,实际上不理解的是我们自己,常人都在我们的场中,用我们的不理解反过来干扰我们。 记得刚得法时有将近两年,我不参加集体学法。因为我一看到大家在一起读书,就想起文化大革命学毛选。我儿子得法以后,因为他是小孩,需要一个学法的环境,就带他去学法点。他参加英语组,我参加中文组,一段日子下来,发现和学毛选根本是两回事。学毛选要求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但是我们学法,仅仅是大家在一起有一个学法的环境,师父的一句话,由于每个学员修炼层次的不同,理解也不同,有时候都对。所以,表面上看上去一样的东西,实质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内涵。有一天,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对我说,法轮功的有些作法和文化大革命很相象,我就把上面这个例子告诉他。他后来谢谢我,告诉我就因为我跟他谈的体会,使他在中国开始镇压以后,他没有相信共产党的造谣宣传。这说明只要讲清了真相,世人是会明白的。 再说,一种赞美只流于表面,不是从心底发出,它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形式,但发自内心的崇敬、感激,却不是形式,不是盲目崇拜,她是有实质内容的。我想这不仅仅是知恩感激的人的一种好的行为,师父的像越多在另外空间也越多,对人对神都是有好处的,当然要画得象,不象就是在造业。我们的画不仅仅是给人看的,也是给神看的,神会看到我们对自己师父的尊重,同时我们向宇宙的众神宣告:师父是宇宙众生真正的主! 当然,师父并没有叫我们画他,这是我们弟子的一片心。师父说:“人类美术作品的创作中心应该是神。”这句话的意义是很深的,我理解她不仅是宇宙各天体、层次的神,也包括很多修的很好的大法弟子的神迹。但是现在很多大法弟子还在监狱中受苦、受刑。把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镇压的残酷这一事实以美术的方式公布于世,让全世界的人都来谴责以及停止这一罪行,是我们有美术创作能力的大法弟子的当务之急。 绘画的过程,就是修炼的过程。只有修去方方面面的执著和后天的观念,才能越来越达到神的状态,才能走向圆满;同时也才能真正在正法中助师而行。师父给予我们的时间是多么珍贵,但我们不能因为师父的慈悲与耐心,不断重复自己的过失,把师父的慈悲当儿戏。有时候我担心,如果有一天,师父不再原谅我,我将怎么办? 珍惜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在神的路上精进,才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望与苦心。 感谢师父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救度。 谢谢大家。 (2004年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