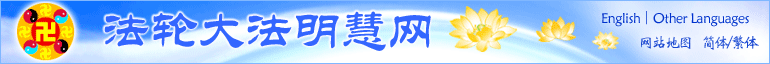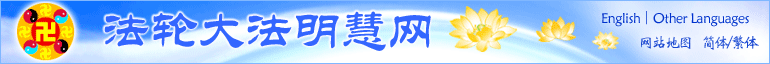|
【明慧网2004年3月8日】我是1996年9月喜得法轮大法的。因那年9月我的哮喘病复发,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心想完了,往年是冬至进九的时候发病,今年阳历9月病就来了,不知我还有几长的活路了。这时,有一好心人告诉我去炼功,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走入了这个场,当我一走入了这个场,他们热情接待了我,教我炼功动作分文不取然后借给我法轮大法资料看,我感到他们是真诚的。第二天我请来了师尊的《转法轮》。我一口气读完了《转法轮》。书中教人向善,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做了好事会有好报,做了坏事会有恶报,我深信这个理是真的。自那以后我坚修大法。和同修在一起,每当我听到他们谈修炼心得体会时,我都深深被他们的高尚品德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也更坚定了自己修炼的目标,立志做个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好人。自那以后,我工作上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为单位节水节电,收废利旧,也不计得失和报酬,也明白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对人友善,和同事间的关系也搞好了,因为大法讲对任何人都要好,处处替别人着想。
就在我活得充实而有意义的时候,1999年风云突变,残酷的镇压和迫害开始了,诬蔑陷害的宣传充满了中国大陆。刚刚开始时,我茫然不知所措。工作不计酬,任劳任怨,对任何人都好,与人为善的正理,怎么成了非法?师父教人向善,做好人,怎么成了错的? 我们单位不但不肯定我的成绩,也开始迫害我。 回想我修炼法轮功以来,工作上做得越来越好,看到厂里的水、电、蒸气没有落实标,生产成本较高,浪费严重,也没有人真心的来管此事。厂里的照明灯一亮就是一通宵,不管是生产还是没生产,反正是亮着,有时白天亮着都没人管,职工上班没有积极性,大多混日子,到月拿工资。做为一个大法修炼者看在眼里,落实在行动上,按照师父的教导,做个好人。为厂里节约,尽量地减少开支。每当我上班,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关厂里的照明灯。可那厂房里的照明灯是十一、二道灯,都是上千瓦的灯泡。一个10吨行车加上一个125吨的脱模机,四个大灯。每当我上中班或上夜班,只要不是生产的时候,我都爬到车上把灯关上,只留一盏照明灯,火车进来能看见路就行。我们那个脱模间真正生产忙的时候极少,平常每天的生产量也就两到三小时,照这样计算每天能为厂里节电5小时,加10个灯是多少电?照算如果是50度电,那么一个月算下来,至少也是上千度电,一年就是上万度电。我修炼真善忍三年,就是几万度电。 另外,我上班为厂里义务收捡废钢铁,至少是上百吨,你说那是上班时间,那为什么别人没事也不收捡。有时我收捡的废钢斗,他们反把渣子往里倒。我们那个脱模的澡塘,外面来洗澡的人比较多,有时水没关上人就走了,我就去关上;有时水管龙头坏了,我就拿绳子捆上,不让它浪费了;工作中蒸气的管理和使用上,都尽量地为厂里节约,这些我从未向厂里要过什么报酬和名利,都是默默无闻做着,为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然而99年7月20日大搜捕开始了,江××要取缔法轮功。作为一个真修的法轮功弟子是什么心情?真、善、忍大法遭到迫害,我的眼在流泪,心在哭泣。当时的情景是中国的全部媒体:广播、电视、电台、报纸,铺天盖地的谎言、诬陷、栽赃,真相被掩盖,正邪被颠倒,许多人相信了谎言,对法轮功充满仇恨,到处谈论。 7.20以后,我被冶钢公安处多次非法抄家、关押、受审。他们强行拿走我的《转法轮》及所有修炼法轮功的书籍、录音带、炼功带、炼功服等。我人身受到多次凌辱。冶钢公安处对我凌辱的恶人有周行保、冯树林,还有一个姓董,我到北京上访时就是他整的材料,使我被拘留15天。还被石灰窑区所谓“转化班”凌辱。他们有一大帮人,有民兵,还有手铐。 2000年5月冶钢公安处姓武的和姓李再次抄我家,强行拿走师尊的经书和我们炼功的照片作为所谓的“罪证”,判了我一年劳教。在黄石看守所关押的二个月里,我受尽惨无人道的迫害。在那里有个叫李所长的审问了我两次后,因我都说大法好,第三天他们就开大会整我,给我上铐子。 姓李的所长叫给我找个最小的铐子,将我的手反背铐上跪着,他还不放过,还用脚使劲踩我的脚后跟,想把脚后跟踩断,铐上后既不能吃饭,也不能解手,更不能睡觉。痛得直撞墙,真想死。到第三天下午他们给我解铐子时,铐子的螺丝帽已锈,一个扳手已打不开,后来用双扳手才打开。 打开之后,那个李所长马上就给我换号子。坐过牢的都知道,换号子是要挨打的。当我一踏进新号子,号头就开始骂我。其他的都是年青的,听到号头这么一骂,就听有一个说,把你的手伸出来看看,当我伸出血淋淋的手,他对着我的痛处就是一拳,痛得我直叫唉;其余的从旁边朝我进攻。打了之后,有人说号头找我叫你蹲下,话没说完,他们就从我的后面照头一脚踩下去,我扑通一下倒在地上,起来后双膝青紫。他们问我为什么进来的,我说为炼法轮功。他们就叫我蹲在湿淋淋的厕所边。不准抬头。 第二天,牢房要干活--扯胶,我的手肿得合不拢,他们就要我为他们端水冲冼大小便。一个人就要冲好几盆水,一个号子十人以上。晚上要听号长让睡才能睡觉,不准睡还得蹲着。有时不准解手。 第四天他们又提出要我“走过场”(折磨新犯人的黑话),要我靠着墙挨打,他们每人打我三拳。打得我全身青一块、紫一块。 在那暗无天日的牢房里,被别人打的次数我已记不清了。我们的人身安全时时受到威胁,受他们的辱骂就更不用说了。后来我的腰被打得直不起来,晚上痛得不能转身,一个多月都不见好,牢霸钱宏还抢走了我的被子。我只好盖牢里谁也不要的沾满细菌的脏被子,从而下半身被感染,又肿又烂,看守所有监控器,他们明知道也不管。我们这些善良的炼功人,在这里总是被别人打骂,可我们从没有打骂过别人。别人说笼中鸟最苦,可我在那里不知比那鸟痛苦多少倍。 后来,我到北京去上访,只是为了说一句公道话:做好人没有错。冶钢公安处恶警接我回来时,强行我交钱买卧铺票和高消费餐旅,而上了车又不许我们睡觉。 大冶钢厂厂长朱献国,善恶不分,开除我公职,在经济上连最低生活保障也不给我分文。同时,我是厂里是一名工龄30年的老职工就为我进京上访说句公道话,他们还把我住的房子拆掉,把我住所的衣物被褥、锅碗勺瓢全部扔了,使我在沙洋劳教回来后无处落脚。那天是腊月廿四过小年,正是三九寒天,外面北风呼呼,我只好在俱乐部屋檐下熬了一夜。2003年8月,我还在马路上过了两夜。 现在我无处安身,经济上极度困难,有时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几十元,就这样艰难地活着。 我因为要做一个好人,江××集团及其帮凶就剥夺了我生存的权利。还说什么现在是我国人权的最好时期,我的被迫害的遭遇就是江氏集团妄想把法轮功“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肆意践踏人权和“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及“反人类罪”的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