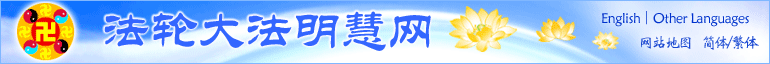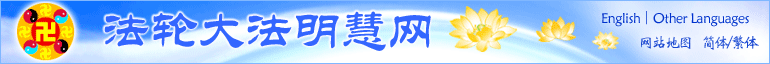|
【明慧网2004年3月23日】我所讲述的几个片断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当我提笔想写下这几个片断时,心里就非常难受,毕竟做的不足的地方太多。我悟到:写出来也是在消除这些邪恶的东西。当我拿笔准备写时,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临死也要挣扎,给我捣乱:当我写到一半时,台灯不亮了;闹钟不响了;最大的干扰是我的身体出现了病业状态,非常重,都写不了字了。我向内找:我觉得没有错,揭露的是邪恶,有很多人还不知道真相呢!当我悟到这一点时,提笔能写了,身体恢复了正常,灯和表又都神奇般地好使了。我写完的当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脱下了一条厚厚的棉裤,是一段段的,不一样颜色,很肥,把它扔了。当时还有个人说:留着吧。我说:不留。醒来后我全明白了。
下面是我讲述邪恶迫害四年多来修炼中的几个片段。在整理之前我想了很久,觉得自己所经历的也不是什么突出的事例,但是,那里有邪恶做的最见不得人的事。我想,把它们暴露出来,也是在消除它们。 * * * * * * * * * * 2000年1月19日,我和功友去北京上访,当时我悟到:我是大法的一粒子,就做一个粒子应该做的。上访的当天下午被送到驻京办事处,那里已经关押了许多吉林的功友。下午三点多,梨树政保科的周彦文和王良把我们带走,并把我们身上所带的钱全部收缴,没出具任何手续,还美其名曰为了我们的安全等,说回去就给我们,至今没还。听其他法轮功学员说也受到同样勒索。 我们一行29名学员全部被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遭受迫害,在那里早上吃的是玉米糊糊,给几条咸菜,中午和晚上是一个似鹅蛋大小的玉米面窝头,玉米面都变质了,还没熟,吃起来辣嗓子,有几条白菜在汤里头游泳。有一天半夜,我和大家一起炼功被管教发现了,恶警体罚我们面墙站两个多小时,然后一顿打骂,接着就用铁镣子把我们两个人铐在一起进行迫害。几天后,恶警开始强迫我们放弃修炼,若谁答应不炼,写保证书交2000元钱就可以回家;说“炼”,就被判劳教一年。他们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往死里打。结果,我被非法劳教。 在黑嘴子劳教所(新生队)20多个人住在一个房间,每天都要坐在水泥地上被体罚:不许盘腿,两只手不许放在一起,眼睛不许闭上,谁不这样做,就遭到犯人的毒打。每天吃不饱,没有上厕所的自由,没有洗涮的自由,没有说话的自由,甚至互相间的一个眼神都将遭到一顿打骂。完全失去了做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 有一天我们炼第五套功法,刚炼一会,便遭到犯人的毒打。它们把一位60多岁姓王的功友拽着衣服从屋里打到走廊;拽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走廊里,我的腿仍在盘着。大队长张桂梅来了,拿着电棍对我们喊叫:“还炼不炼了?”我说:“炼!”它们就用胶带把我的嘴封上,用电棍伸到衣服里边电。 我被提前分到2大队,在那里我们被强迫每天干16—17个小时的活儿。上厕所、洗涮、吃饭,慢一点儿,就会遭到队长和犯人的打骂,没有一点儿人身自由。自从到了2大队,我天天晚上炼功,其它班也有炼的。姓强的管教知道了,把我叫到队部。问我为什么炼功,并说这里是强制的地方,不许炼功。我说:“我没有犯法,我是炼功人,我当然得炼功。”他说:“你一来我就知道你是最顽固的,最有煽动力的。”边说边拿起电棍:“我早就给你准备了一个最大伏的电棍。”说着就电我的嘴和下颚,穷凶极恶地喊:“我叫你煽动,我就电你的嘴。”电棍电到我的脸上,心里有一种特别难忍受的滋味,感到心要跳出来了。那时,师父还没有发表正法口诀,我就背“世间大罗汉,神鬼惧十分。”(《洪吟》)当我想到师父为众生承受的不知比我重多少倍时,感到不那么难受了。直到电棍没电了,累得强管教上气不接下气,才罢休。回到房间,几位功友看到我的样子,都哭了,我的脸和嘴都变形了,用手一摸感觉有油,还有一种烤焦的糊味。同我一起被电的是一班的杨淑梅,她的脸上也被电得往外流油,上半身的前胸、后背被电得没有好地方。第二天,因为我俩被电的事全大队有一半功友绝食抗议,我也绝食5天。 强管教怕我炼功,就命令犯人每天收工后用绳子把我的双手绑在床头上。干一天的活,翻不了身,腰疼的象折了一样。早上起床松开时,很深的绳子印一天也下不去。由于长时间被绑,血液不流通,手雪白的,发麻,干活时也麻。有时她们绑得很紧,到半夜时绳子自动解开了。我知道是师父在呵护着我。 恶管教还经常弄虚作假,平时为了多得到奖金,没日没夜地叫我们干活,等有人来参观时,把我们关到一间小黑屋子或库房,就伪装出一副文明管理、民主人权的假象,欺骗世人,实际上是做着最见不得人的勾当。它们在劳教所门口挂一张大法师父像,接见的人得骂师父,不骂不让见,有的学员家属宁可不接见也不骂师父。 就这样,一年过去了,我虽没有妥协,但也没有以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来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冲出魔窟,这也表现出我对法认识不足的一面,最后我被无条件释放,重新汇入正法洪流。 2001年3月8日,我因在北京发放真象资料,被恶人举报,送到北京市房山区梁乡某派出所。它们问我的名字,从哪儿来,住在哪儿。我说:我叫大法弟子。恶警气急败坏地说:看我们怎么治你,在我们这儿没有一个能挺过去。它们把我背铐到暖气管上,脚尖刚好挨地,凶狠地对我说:“我看你说不说。”然后拿起电棍电我的大腿内侧。另外几个恶警还嬉皮笑脸地说再往上点。我听到这话心里真难受,比电棍电得还难受,这哪是人民警察呀,纯粹是一伙流氓。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失去生命,我也不会说出一个字。我在心里背法。它们一看我还是不说,就把我吊到外面的铁栅栏上,过一会又把我吊到电线杆子上,然后再打我,我被打昏过去了,它们就用凉水浇,最后我被关进房山区看守所。 一到看守所,我就开始绝食抗议非法关押,第3天它们就开始灌食。它们说,我最顽固,要找一个粗管子(加重迫害)。当时我想:我就是不配合你邪恶。于是我反抗不配合插管,它们把我铐在床上,又叫来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刑事犯来帮忙,用绳子把我的腿、身体全绑上,给我灌食。我就想:我这么纯净的身体怎么能要你们这些黑黑的东西!它们使尽了招也灌不进去,只好把我送回号里。 在看守所里,有位哈尔滨叫李淑兰的功友,65岁,已经绝食3个月了,它们也不放人。 在我绝食的4、5天里,它们灌食一次次失败,于是对我进行新一轮的迫害,给我戴最重的手铐和脚镣,手和脚是连一起的。第7天,它们想办法治我,把我吊到南4号,利用犯人进一步对我进行迫害。凭着对师父的正信,我度过了一个个的难关。绝食20多天时,邪恶之徒再也不管我了。我悟到:绝食不是为了丢掉人身,是为了证实大法,我还有责任在这里,我得跟犯人们讲清真相。于是我停止了绝食,在生活上、精神上关心她们,并不断地给她们讲清真象。后来有一个犯人知道了我是东北的,告了密,我被非法判了两年劳教。 2001年5月29日,我被送到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那里的队长姓秦,南方人,40多岁,非常狠毒。它让我写保证不绝食,不炼功,我不写,它就打了我一顿。它要求我们走到门口得喊“报告”,我不喊,它又打了我一顿,然后就让我到放风场蹲了一下午。 在那里我们被强迫劳动(包一次性卫生筷子),每个人有定额,完不成不让睡觉,从早上4点开始干活儿,直到晚上11—12点才收工。上厕所都受限制,有的人都便到裤子里去了。恶管教不许我们说话,也不许随便喝水,毫无人性可言。这里下队前,我们要把衣服全脱光了,连短裤都不留,全身检查一遍,有特殊情况的连卫生巾都不让用。 劳教所后,每个学员马上有几个犹大包夹,围着说诬蔑师父和大法的话,用它们的理解断章取义地说,还假惺惺地关心你。不放弃修炼的学员至少三天三夜不让睡,我知道的最多的长达17天不让睡,不让洗漱,不让用日用品,一顿一个窝头几条咸菜,上厕所包夹都跟着。在那里,如果它们发现你看别人一眼也得挨打,不让回寝室,回去也是等半夜12点以后,睡两个小时就被叫起来。劳教所的恶警非常怕不放弃修炼的学员跟走了弯路的学员说话,生怕走弯路的学员通过交流,再醒悟回来,重新修炼。邪恶之徒也深知,它们的迷魂药是不长久的,是站不住脚的。 三天内要不转化的学员,就被恶警视为顽固分子,再换几个犹大。它们是连骗带吓唬,利用疲劳战术加上伪善。在这种情况下,学员主意识稍一放松,就容易上它们的圈套。五天后学员还不写三书,它们就找队里。它们认为最有效的是轮番洗脑,不只是动嘴了,动手打,面墙罚站、蹲着,整天不让合眼,稍微一合上,就冷不防打你一下,有的功友就这样被吓的精神都失常了。 所有的这些手段也没能让我屈服,无论它们说什么,我就是不听,我就是一遍遍地背法。我心里明白,丝毫不能马虎,人心出来,就会面临走弯路的危险。我背“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这段法帮助我走过了一个个难关。 北京市女子劳教所经常有人参观,每当这时,管教马上把卫生筷子藏起来。我顺便说一下所谓的“卫生筷子”:筷子在地上被随便踩;有的人长了疥疮,用手乱抓一气疥疮后又去包筷子;没包好的大包的筷子拿不动在地上拽;打包是用脚踩。筷子藏好后,就是没完没了地搞卫生。如果哪一天改善伙食了,那就是有参观人的来了。遇到有宣传媒体来这儿参观,管教提前把人找好,背好了台词,对着镜子练。有外国人来参观了,把坚定修炼的大法弟子关到一间小黑屋,挑几个所谓表现好的到操场上跳“经络操”。听说有的还回答了外国记者的采访,内容不详。这里还有集训队,6个月不写三书的学员就被送集训队。一般队里不上报不放弃修炼的人数,怕影响转化率,得不到奖金。听说集训队有各种迫害方式和刑具,有开飞机、开汽车、坐铁笼子。坐在铁笼子里四处不能动,大小便都在那里,非常苦,可见那里的邪恶程度。 后来它们也不强迫我放弃修炼了,但是有监视,不许我和别人说话,说了就告诉队长,就又要去队部洗脑。我班老年人多,我是年龄最小的,有什么重活我都抢着干。洗衣服,打水,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无论在哪里,什么环境下,我都向内找,都要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表面上看还不错,其实,从修炼的实质上讲,这个时候我已经掉下去了,这不是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否定旧势力的状态。就这样,我沉默了一年多。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队长对我很放心,这说明我的行为符合了它们的心愿。 2002年6月,有一次队长带我们三个人去北京市大兴区法制培训中心,在那里我结识了许多功友。功友告诉了我发正念的口诀,又给我讲了发正念的重要性,因为一年来我没有和功友接触,根本不知道发正念,当我第一次发正念时,把我吓一跳,只看见有一排排的小兵,背着东西,手拿着很长的棒子从四面八方过来了。 我还有幸看到了师父的《在北美巡回讲法》和经文《正法与修炼》。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法了,当时的心情是无法用人的语言形容的。我想这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不让我再继续沉默承认旧势力的迫害,这是给我的机会呀。 我想我得想办法把经文带回去,让功友们都看到,我有这个责任。我用最小的字把经文用最快的速度写好,放到安全的地方。这里经常搜房间,要是搜出来会有很多无辜的人受牵连。我想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情,不允许邪恶迫害,因为我们一动念旧势力看得很清楚。回队后,每次不搜身,而这次非常严,但是我心里非常平静,我带的经文没有被发现,另两个功友都为我捏了把汗。这都是师父在呵护着我们。 回到班里,我们把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的内容和发正念的重要性都告诉了功友,有几个功友又重新回到了修炼中,都留下了热泪。自此,我们班的功友全都开始天天背法、发正念。我们班的学员每个人都利用上厕所、打水打饭等机会与其他班的功友交流、切磋,特别对那些没有了正念的学员,告诉她们不要再这样下去了,要多背法、发正念。我把《正法与修炼》写成纸条传给每个班,这时邪恶知道有经文传进来了,不知所措,还以为是接见带进来的呢。再有接见时,回来后把我们带到水房,让我们把衣服全脱掉检查一遍,什么也没查出来。这时邪恶之徒就清间,我们班的经文都放在我这儿,因为我在上铺,一有机会我就拿出来发给功友,看完了再收回来,放别人那一旦发现就会被加期。开始规定一周清一次房间,发现有经文后,一周清两次,而且没有固定时间,说清就清。 到2002年11月8日,邪恶之徒找一个借口,放我回家了,我又投入到了正法的洪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