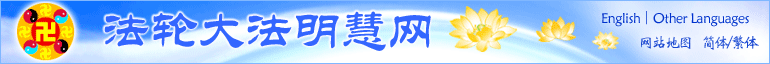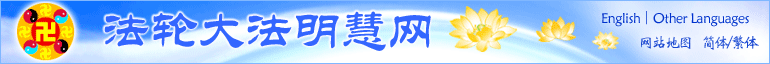|
【明慧网2004年3月17日】修炼前我是个病魔缠身的人,从头到脚无处不是病。我有神经性头痛,无药可治。我的左腿全是黑的,整天脚胀、发烧、疼痛,难受极了。川医的医生已下了结论:你的脚没法医治,肌肉都僵硬了,细胞已坏死。我真是活得非常痛苦,生不如死。就在我投医无门时,99年农历正月初九我喜得大法,我每天去炼功点,一星期后,我的腿明显开始软化,我真是太幸运了!身体一天比一天轻松,到现在周身的疾病全没有了。是师父从苦海中把我捞了起来,是大法使我获得了新生,用尽人间语言也无法表达师父对我的救度之恩,我只有精进学法,做好师父要我做好的每一件事来报答师父的慈悲苦度。
99年7.22下午2时,派出所的警察到炼功点来收书,叫我们3点钟看电视,当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他们为什么收我们的书,他们说等会儿看了电视你们就知道了。3点钟电视播放了诬蔑师父的节目,我根本不相信,但我很困惑,法轮功从92年传出,7年当中上亿人受益,为什么今天一下就不好了呢?看过电视后,警察宣布从今天起不准炼了。当天晚上我没有炼功,心情乱极了,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但我冷静下来后,我细想:师父是教我们做好人,做好人没错,我的身体变好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我要继续坚持学法炼功。过后和功友切磋,才知道是江××丧尽天良迫害法轮功。 2000年听说好多同修都到北京证实大法,我想我也是修炼人,我也受益了,为什么不去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呢?于是我约了两个同修,于2000年6月28日去了北京。当时正是敏感日,车上和站上查得很紧。在西铁站查身份证时,我们被挡住了,下午被送到驻京办事处,叫我们蹲在坝子里。晚上住进一间10多平米的小屋,里面关押了三、四十人,只能挨个坐下,无法睡觉。白天邪恶之徒不准我们炼功,我们都不听他们的,就把我们赶到坝子里曝晒。当时北京气温很高,40多度,我们几十人人齐声背论语,背《洪吟》,邪恶之徒敲打盆子想干扰我们背法。后来昏倒了几个人,他们仍不放我们进屋,还说:你们背吧,把天背下雨了,你们就进去。当时是大太阳,我们没理他,就继续背法,过了一会儿,天一下变了,乌云遮住了太阳,雨大点大点的往下落,我们齐声高呼:下雨啦。当时欢喜心出来了,雨一下就停了,但恶人还是震惊了,把我们全放进屋里。我想这是师父在保护我们,师父无时不在我们身边,我落泪了。到了第四天,成都的警察将我们接回,随即送至成都戒毒所关押。后来又把我们关在一个又脏又潮湿的留置室,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准上厕所,蚊子多得很,家里人送来矿泉水和蚊香,但他们不让点蚊香,任蚊子咬我们。关了我们48小时,我们讲了为什么我们要去北京上访,因为我们是受益者,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我们通过实践,炼法轮功确实是百利而无一害,我们去说句公道话也有罪吗?最后他们把我们放回家了。 2000年11月23日半夜,我和老伴出去贴法轮功真象标贴被巡逻警察所抓。他们把我们带到派出所,随后就抄了我们的家,拿走了收录机和炼功带。当天上午就被送到新都看守所,由于警察不知道我丈夫也修炼,拘留了他7天放了,我被刑事拘留30天。 12月28日由于一同修承受不住迫害,说出了我们,恶警又来把我和丈夫、儿子一起带到派出所,并抬走了女儿的复印机。他们把我们分开审,还打了我丈夫。30日下午,在派出所的坝子里召开大会,把全部炼功人、全镇的村干部、群众都叫来了。会后把我们和三位北京来的同修都戴上手铐一起送到新都看守所迫害。看守所期间受到非人的待遇,吃的是水煮菜,烂米饭。里面的东西贵得惊人,高出外面几倍,每天还要交四元钱生活费,其他犯人不交钱,只收法轮功学员的钱。不准我们炼功,每天做纸袋、粘酒盒、做针药盒子、叠书页,做到深夜。当时正是数九寒天,我们号里有8个炼功人,我们一起炼功,恶警不准炼,我们没理她,她就把我们全部弄出去跑、罚站,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引起其他犯人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但我们还是给号子里的犯人讲法轮功真相,遇事帮助她们,关心她们,她们也不为难我们了。恶警看这招不行,又换了更毒的招术,只要看见有人炼功,就叫犯人打,不打就从楼上往炼功人身上泼水,泼得每个人全身湿透,还不准晒。只要有人盘腿坐着,不管是否炼功,就往床铺上泼痰盂里的水,泼得又是痰,又是烟头,很臭。关了45天后,当地派出所把我接回来,又接着办洗脑班,叫我写保证,我不写,就又被送去非法关押,我们没有一个人被吓倒,最后还是堂堂正正地回了家。 刚回家17天,派出所恶警杨怀忠把我和丈夫骗至新都公安局,他说有点事叫你去证实一下,一会就回来。结果我被非法刑事拘留一个月,丈夫被非法判劳教两年,被送到绵阳新华劳教所,直到2002年7月14日才放回来。 走到了今天,我们始终坚定我们的信念:做好人没错,法轮大法是正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