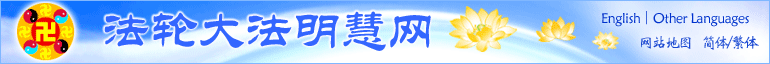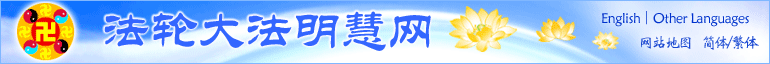|
【明慧网2004年3月11日】我是沈阳大法弟子,经历了劳教所的迫害,现将我和同修抵制迫害的经历写出来。
1999年7月,居委主任和当地派出所5个人突然半夜闯入我家,进院看见我爱人出来,就把他推在墙的一角。进屋叫道:“把书交出来,快点,配合一下。”我说:“没有书。”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他们在屋里乱踢东西。我说:“有搜查证吗?”他们不听,就要动手拽我。这时邻居一个小伙子跑过来,推开他们说:“干什么?她犯什么罪了,凭什么?有文件吗?”这些人马上过来打他,拽他就想带走,他妈吓得坐在地上哭。后来,来了不少邻居,都说我是好人,没做坏事,这样派出所的人才开车走了。事后派出所还派人来到我的单位骚扰。老板说:“她是好人,工作认真负责,表现突出,谁都说她很善良。” 2000年7月末,我依法上访,被关押沈阳龙山教养院。当时是伏天,天气很热,27人关在不足40平米的小屋,坐小凳,不准走动,学院规,昼夜被监视,天天被强制灌输宣传,听诽谤大法的广播。为抵制迫害,我们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要求无条件释放。院长孟伟说:绝食就灌,看谁受罪。一天上午十点左右,他们先把我带出去,指使大队长申义、季玉坤等4个警察打我,揪住头发拳打脚踢,然后按在床上,用一根手指粗的管子插入鼻孔开灌。当时在没有医生,什么医疗设施也没有的情况下,几个普教按住头和四肢,我喘不出气来。在这期间感觉是在生死线上挣扎,但心中有一念,不能死,还要做很多事呢。灌进去,喷出来了,喷在他们身上,我满脸是血,我被推在床上。这样的事件,半年发生过6次,每次收费50元,家属看望一次就要交500元,还有伙食费每月600元,家里罚款5000元,罚村政府2000元至今未还。男恶警向我们脸上吐唾液,倒热水、凉水,后来戴手铐送王家庄看守所。 晚上一个警察过来讲:“你们这些人怎么还不明白,不管你们违没违法,来到这里就是犯人,还讲什么权利呀?太天真了,咱中国就这样,要么到外国去呀?就是死也没人管,中国人最臭。但是呢?我们还感谢你们“法轮功”,自从你们来了,我们还开出支了,以前亏损,现在好了。”我和他讲善恶有报是天理,“每个人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他听了,只是苦笑了一下,没再说什么走了。他们搞强权,以权代法、以言代法,这样下去国家怎样、社会会怎样呢? 2000年12月26日晚4:30分被非法送马三家教养院,非法搜身及一切物品。然后邪恶之徒开始实施所谓的‘攻坚’战,即转化,逼迫学员放弃信仰。利用它们信得过的人围住我,拿来一些假经文,断章取义地邪悟、乱悟。然后讽刺、挖苦,目的是让我说假话、办假事,从而放弃修炼,要的是转化率。因我仍坚持不放弃,不和它们配合,被进行严管,24小时监控,强制看诽谤大法的录相片。不准走动、说话、面壁、不让睡觉,企图在意志上毁掉我。由于长期遭受的迫害和精神压力,总在阴暗潮湿的水房里,使身体受到了很大损害,长疥,白天劳动,晚上也休息不好,勉强能休息4个多小时。当时有人让我去医院,我没去,心里有一念,炼功人不怕这些磨难,不去想它。就这样他们还要做‘转化’工作,一年多的时间才恢复。 2001年1月中旬,全所召开“政策兑现大会”,放走一批放弃修炼的人。当时来了很多记者,还有中央的,一个事先被安排好的人讲话(这个人是辽宁省朝阳人,叫王春英),当她讲到干警如母亲关怀,不打骂……女大法弟子被扒光衣服扔进男监舍是谣传时,突然站起来一个学员,高声喊:“你说的是假话。”话音刚落,警察指使一些学员上来捂住她的嘴,按倒拳打脚踢,拖了出去(这位大法弟子叫邹桂荣,辽宁省抚顺市人)。事后,一大队未转化的10名大法弟子被带走,押送辽宁省大北监狱地下监管医院迫害(邹桂荣、王丽、周艳波、苏淑珍、赵素环、尹丽萍等),后来我被分到原邹桂荣所在分队,一天大扫除,在一个床下边发现一个日记本,是邹桂荣留下的,就记一篇。内容是99年*月*日,队长(张秀荣、周笺、黄*)用电棍电她乳房、阴部和其它部位,隔十分钟电一次,共三个小时。半个月后指使别人体罚她,按住头往便池坑撞,边骂、边讽刺、挖苦。 2001年春节放几天假,一个叫门丽静的人(大连人),她是号长,不让我们室几个没有转化的看电视,说:“别想轻松,抄书(诽谤大法的书),抄完读几遍再看电视,谁不抄还是面壁。”我说:“过年了,还有没有人性?干什么?想凌驾法律之上吗?宪法还讲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呢。”她一下站起来说:“你又皮紧了。”就上来要打,被一个年岁大的老学员拦住了。马上又上来几个人按住我蹲下四个多小时,当时站起来都困难。这件事反映给值班警察,却没有回音。 2001年10月份正值秋天,扒包米,早上8点出工,到黑天才能收工。9个多小时,除半小时吃饭外,不准休息,天气有时不好,下雨就顶雨扒,也不许落后。20几天的时间,我身上长疥,晚上回来,裤子脱下来带血,粘在腿上,就这样也没有让我歇一天。 2001年一大队住处条件很差(以前是戒毒所),水房和卫生间连在一起。150多人用一个卫生间,一层楼卫生间4个坑,5个队长一个坑,这三个坑,就很挤。有个学员不知队长那个不准上,去了,干事王素铮马上说:“别上这个,不知道自己是干啥的嘛?也不许在这水房洗澡(没有浴池),再叫我看见,加期。”学员说话声音稍大一点,她就喊:给我闭嘴。 由于对我迫害较重,我总是便秘,蹲的时间稍长一些(二十几分钟),门岗的四防(学员)张素斌就骂道:“快点起来,不要脸,站在毛楼不拉屎。”晚上邪悟的人都在走廊做转化工作,4、5个人围住一个“未转化”的。有时恶警王乃民走过来,看看这个,指指那个,对着坚定的大法弟子讽刺、谩骂。 2001年11月份一个星期天,来了一个以前和我在龙山认识的学员,叫邹本兰(沈阳的,50几岁)。她想和我谈谈,队长张卓慧同意了。到办公室四楼,还有一个室的王绍同和另一个学员。我们四个刚谈半个小时左右,队长张卓慧上楼就喊:“你给我听着,来到这干什么?就是“转化”,给我写保证、决裂,转也得转,不转也得转,别费劲了。”我说:“逼转化率吗?你违法,说假话,我从来不会。”她气得喊:滚!我看到她中毒很深,给她写了洪法的一些资料,叫她知道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别再助纣为虐,善待大法弟子,能有个好未来。回到分队刚坐好,恶警王乃民过来说:“面壁,治不了你吗?”坐了一会,我起身站起来,拿点手纸。她骂道:“不要脸,谁叫你站起来的,今后不许你乱讲话。”我说:“说话是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剥夺。”他说:“闭嘴,大伙都听着,今后她不遵守纪律,乱讲话,给我记上,加期、记过、严管。” 2002年5月份,所里来了很多检查团和参观的,他们掩盖迫害、造假,也不让劳动了,不做工作了,布置寝室。平时四个人一个床的被子拿进仓库里两个(两个单床合在一起,横睡4个),这样显得没有关押这么多人,一个室八个大床(三十几个人)床头也少了十多个,未转化的隔离不在室内,关押隐蔽房间。布置图书室、活动室,改善伙食,让一些转化的邪悟者对摄像机镜头,讲教养院如何如何好,走后一切还照旧。还搞什么献爱心活动,动员学员给一个医院患白血病的小男孩捐款,不写姓名,却写上马三家教养院。有的新来的学员很困难,她们总动员学员给捐款及物品等等(一切由分队管),给学员经济造成了很大的负担,贡献大的当然要减期了。 2002年6月份,我悟到不能戴牌和穿校服(囚服),我说:“我没有违法,不是劳教,这是强加给我的罪名,我不能接受,这不符合宪法。”大队长张秀荣叫一些人将我捆绑,说:“给使劲打,我负责,谁不打,给我加期。”然后,他先动手拳打脚踢,踩肚子……一连殴打几十分钟,抬到一个寝室(没人住的),我的衣服都被打扯破了。她喊:“再给她买一套,去她包里拿钱去(现金60元),快点。当时衣服被扒掉了,鞋也打没有了,只剩下胸罩和裤头,摔在地上。当时腰都不能动,过一会,让(四防)门岗的人给我戴上手铐,带到一楼小号,铐在暖气管上,晚上身穿单衣冷得寒颤。室内阴暗潮湿,不许睡觉、洗漱,12小时上厕所一次(上厕所开铐,还得态度好,否则不开)。我说:“你们执法犯法,邪恶,会遭报的。”张卓慧说:“不开,不能去了。”恶警王乃民进来讽刺挖苦地说:“怎么样?很舒服吧,还有更厉害的呢,服不服啊。”我说:“你们这才是真正违法,不配穿警服,政治流氓,不久的将来受到审判。“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王乃民说:“你还敢教训我,我说加期就加期,看着吧。”然后广播室讲了很多强加的罪名。 还有一次上洗脑课,我因身体不舒服,和队长张卓慧请假。她马上说:“不行,死也得去。”让一些人拖着抬着去上课(那天上课在食堂和我居住的楼很远,下三层楼,还得走很远),从三楼下去,衣服和鞋都拖掉了。当时还是雨季,拖到操场放下,当时地上都是水,浑身泥水,又抬到食堂。我坐在地上就对学员说:“这样迫害,还上课吗?”上课的警察手持喇叭叫学员注意听,不要受我干扰。我抓起凳子扔了过去说:“你们迫害无辜的百姓,简直没有人性,天理不容。”队长(警察)张卓慧上来就打耳光,将我又拖出去了。和一个恶警耳语了几句,到一楼医务室和一个姓陆的警察(直属队队长)大声说:“学员大家都来看看她的形象吧。”然后让一个得过精神病的学员(邬素贤,锦州)不停地骂了大半天。晚上,值班警察代玉红揪着我衣服,推着我上三楼,关进仓库里(屋里装有做手工活的料,这些料都有化学药品味,很呛人)。她说:“看看你连衣服也坏了,鞋也没了,泥水一身,象人吗?到这来,想不转化,挺得住吗?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告去吧,今天我值班,你别想得好。”晚上我要上厕所换手纸,肚子痛。她马上说:“不行,告诉你,象你这样见得多了。99年我带过班,比这厉害,看你熬多久。” 后来有新学员进来,才转到卫生间去继续体罚,还是不让睡觉,长蹲、不准移动,就离便池二米远左右,一天给两个玉米面饼子(不放碱很硬),有时没咸菜。有一天,我大声讲:“敢不敢把你们的这些行为让参观的检查的看一看呢?敢不敢曝光,不是总讲公平、公开、公正吗?”又一个值班警察过来喊:“别喊了,谁不给你咸菜了,是给忘了吧,给她点咸菜。” 2002年春节前夕,劳动几乎天天加班到晚上十点,一天要干13个多小时,室里有十几个身体不好的和年岁大的学员,有些干不动了,靠在床上。我被做工作十点回来问她们:“怎么还不就寝。”一个学员和我讲,超负荷劳动,得到二十九才能干完。我讲:“这就不符合劳动法,不符合规定。”恶警王乃民进来说:“跟我去办公室。”我说:“走,看一看劳动法,以理服人,反正讲公平、公开、公正。”到办公室一看屋里4、5个恶警,她大声说:“站好,不准再说话了。”就开始动手打我前胸,边说边打。教养院不是养老院,你们是劳教知道吗?还有你们说话的权利吗?就是服从,理解不理解都得服从,否则整死你,送大北监狱就是我们一句话,你去告啊,我们怕什么?有人撑腰,你们呢?可就惨了,“鸡蛋碰石头”。两个小时后,才放回分队,过几天发现我前胸青半个多月。 2002年秋天,所里又包几百亩地,扒包米。这次家里几乎没留几个人,都下地了,坐车到很远的玉米地里下车,有的学员背着身体不好的学员(岁数大的,七十多岁)。有一天刚到地就下起大雨,警察张秀荣说:“都站道上,不准动。”后来雨小了,顶雨干,有的学员身穿半截袖,冻得打哆嗦,有的跪着扒,直到扒完。直属队一个学员说:“口渴,想喝水。”她们队长(陆*,很胖、戴眼镜)说:“回去喝,总喝水,干多少活?还以为敬老院呢,劳动教养院,快干。” 还有一个叫李冬青的(沈阳大法弟子),99年10月份非法关押,只因为她总记录被迫害的事实(几乎我们室人都看过),日记本记了3本。她身体不太好,有时躺在床上写东西。有一天来人参观,要上楼。大队长张秀荣、周笺、扬晓锋、张卓慧、王雪秋(分队长)马上跑进来,上床把她往下拖,拽到办公室,抢笔、殴打她,记录本被抢走了,手被他们用笔尖扎。然后把她关押隐蔽的房间,用以躲避探视和检查参观的,关了将近三个月。2002年8月份,全所召开整治劳教场所秩序大会,非法批捕李冬青、李黎明、宋彩红,现在辽宁省大北监狱。当时动用所有警力全副武装,把所有学员围住,非法给不转化学员分别加期。还有从龙山教养院来的学员,加半年期,非法给我加期8个月。 还有一次,我不去上洗脑课,他们把我绑在床边,强制听诽谤大法录音。一个叫王玲的大法弟子从分队路过上厕所,听到录音,立刻冲进屋,给插销拔掉了。说:“别再对大法和师父犯罪。”出去被一些人拳打脚踢,带到一楼小号,戴上手铐、铐在长凳上,几天几夜不让休息,体罚将近几个月。 2002年元旦前夕,食堂吃饭。二大队一个学员站起来说:“在屋不让说,我可以在这和你们队长讲了吧,你们总讲公平、公开、公正,那……”话音未落,值班队长(项*,现在负责广播室)马上制止说:“不准乱讲,堵住她的嘴,还敢乱讲。”唿啦一下上来十几个人,一阵拳打脚踢,打倒在地。当时她脸青色,有些变形了,拖了出去,以后没回分队。 有一次,我在的分队尹丽萍(铁岭人)吃饭时,站起来说:“我们不能在这吃饭了,应该释放回家。”唿啦一下又上来十几个人就把她拖走了。听说她被警察打得大小便失禁,半个多月,还胃下垂,走路都走不稳,打点滴一个多星期左右,吃点东西胃就痛,脸色腊黄。后来我在分队学员捐款给她治。 他们迫害学员从不手软,使用文革时的手段,挑动群众斗群众。要是表现好的减期。如:门丽静(大连的)、万冬霞、衣庆芳、刘慧君、李秀平、马桂芝等人。而心软的、善良的、关心学员的凌海大法弟子刘玉芝则被加期三个月。我在分队有个凌源的张桂华为了我的事,她总哭说:“你太善良了,她们对你这样,你还不恨她们,说她们是被利用的,还给她们讲法理。谁善呢,我看出来了,还是你是对的,这么折磨你,你还没病,身体还好。我就不行了受不了折磨,也只好放下了。”我们总鼓励她,让她做好,别落下。 2002年12月20日,所里又来一次整治劳教场所秩序大会,强制转化,一个一个过筛子。我所在分队有个叫张永杰的,把她带到一个黑屋里,手脚被捆绑一天一宿,后来昏过去了,用水泼醒,继续迫害(迫害她的有郭霞、崔素芬、白静等人),直到承受不住。听说一大队有个叫胜利霞的大法弟子,给她腿绑(盘腿姿势)24小时,手也绑上,后来她吐血了,直到承受不住。还有的学员两手被铐在一根铁管上吊铐。那一次,包括我在内很多学员(200多人左右)没把握好,但我们很快清醒,严正声明所有不符合大法的言行作废。 2002年的一天,所里邀请沈阳文化局来放诽谤电影,她们又拖着我去看,队长张卓慧在身边,门口都有男警察把守。我身边一边一个人(万冬霞、崔素芬)按住胳膊和肩,强行我坐下。电影声音很大,振耳,我的头很疼,就想出去。我和大队长说:“不行,头太疼了,我走。”她马上说:“不行,死都得看,就迫害你了,快告去吧。”那两个人使劲按住我。我说:“编排的在电视看过了,都不是炼功人的行为,这是诬蔑、造假。”她们俩捂住我的嘴,不准讲话。我挣开她们的手,喊:“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横扫乱法烂鬼。”演完他们把我拖回到办公室,叫他们这两人作证,叫我再讲两遍。我讲了,两个干事记上,她们说上报加期,问我后不后悔。我说:“我决不后悔,只是讲真话。”02年元旦,普教来演节目,让我去看。我说:“不去。”她们说:“你不去能行吗?扬景秋(大连的)揪住我边打边推下楼,大队长张秀荣表扬她。听说对她很满意,叫她当室长。这个扬景秋对分队学员暗中监视、记录,报告大队长(队长张卓慧都听她的)。她总是岐视、谩骂学员。有一次,一个学员叫马凤珍(锦州),说她说了不该讲的话,一些学员指责她,吵了起来,气的她躺在地上大哭、大闹,后被拽到办公室。室内学员压抑,不敢讲话,默默干活。 2003年2月份的一天,沈阳市公安局来人找我,我去了。他们说:“这一次没别的,写好家庭住址。再填个表,滚个手印。”我写了住址,拒不填表和滚手印。我说:“无条件释放。”这时恶警王乃民骂道:“别不要脸,还要加期呀?不填就强制。”回头对他们说:“她就这样,什么都强制,简直精神病。给我动手,按住她。”干事汤艳、分队长张卓慧、扬晓锋和公安局三个强制滚手印。公安局人说:“你不签,我们给你签,其实签不签,都生效。”第二天他们还逼迫我写什么七敢,又指使邪悟学员郭霞(昌图人)、崔素芬(阜新人),用她们手握紧我手强制写。 有一次所里开展什么军训,邀请沈阳雷达战的官兵,训练学员。年岁大的也强行训练,打太极拳,如不服从,记过、加期。我和队长谈:“我身体好,不需要,我不想和你们争斗,你工作,我修炼,不符合炼功人的行为我不做。愿意怎么样,随便吧。”她马上说:“不行,上边还要来检查,我不受罚吗?”不做还强制,吃苦头。这次她们还是体罚,不让睡觉,白天水房,晚上在卫生间,派人轮番监视,(两个人一班,全分队90人轮),不准移动位置,一动不动、面壁、不准讲话,有时四防(门岗)进来骂上几句。有一天我肚子疼,靠墙一会,大队长马上拽住我推出来说,坚持不住,转哪?月经来潮换手纸,刚蹲下,值班队长代玉红拽起我说:“不行,挺着,今后你没有自由,上厕所得我们允许,后天我下班了你再上。”那天晚上我栽倒在地上,他们还不罢休,拽起来说:“站好,要么长蹲。”当时正是正月十五,20几天都没有上床休息(每次都半个月之上),后来白天体罚,晚上允许上床。但都不在寝室,把手工活的任务数分给未“包夹”的学员,每次都很多。 到2003年4月份我被无条件释放回家。
|